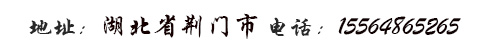我那医官爹爹让贵妃先怀上龙胎,皇后怀恨在
|
1 重阳节刚过没多久,我爹照例进宫给嘉贵妃请脉。 晚间回到家之后整个人不太对劲儿。 平时脾气算挺好的一个人,回家之后就把奉茶的小丫头给骂了。 两个日常在近旁伺候的姨娘连大气都不敢喘,躲在书房外面咬耳朵。 直到我从府内西面的草药园子出来,就被两个十分晃眼的妇人一左一右架住。 我娘早逝,爹爹也没续弦,眼下府里只有三位姨娘。 其中一位是我母亲从娘家带来的贴身女使。 如今上了年纪身体欠佳,住在草药园后面的僻静院中不大出门。 眼前这两位,属于比较闹腾的。 “卿卿,你可来了。”桂姨娘吓得掉起眼泪,头上珠钗闪得让人心烦意乱。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我下意识把她往外推推。 她这人平时挺节省,就算是往自己身上也不太舍得花钱,用的胭脂水粉质量都不怎么样。 “你是你爹心尖儿上的人。”焦姨娘率先哭出声,没等桂姨娘开口便将话头儿接过来,“他再不高兴,看见你也高兴了。” 穿到这个世界的第七个年头,我可太了解这位盛大人了。 没错,我是穿来的。 七年前,我值夜班抢救病人,医院急诊室。 再一睁眼,自己正在被一个古代中年大叔抱着哭。 就这样,我重新活了。 医院左院判盛时珍的长女。 当时我大病初愈。我爹对着我娘的牌位用列祖列宗起誓,要盛家绝世医术全部传授给我,以告慰我娘在天之灵。 盛家是医药世家。 我爹的医术是一等一的高,可说句大不敬的话,他为人也是一等一的渣。 “我才是我爹心尖儿上的人,那我爹的心,也确实够大。”我冷哼撂下一句调侃,甩开两个妇人,大方地走向书房。 我倒不是真跟两个姨娘过不去。 这么多年她们二人对我这种口出狂言的作风也习以为常。 她们进府有些年头,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可论起对我,确实是当做在家的娇客女儿那样担待。 顶多就像现在这样背后嘀咕两句,退到远处等着看戏,从未动过什么歪念头。 2 “爹?” 我踏进书房往里瞄一眼,只见他老人家正端坐太师椅上,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城南咱们家的生药铺子掌柜说,没收到账房这月份例的进货银子。”我恭敬行个礼,直接开门见山。 听到这话他抬抬眉毛,没说话。 七日前,他在清音坊给一个歌姬赎了身,安置在盛府后院三仙巷的一处院子里,以为能瞒天过海。 “这事要是让两个姨娘知道,您猜会怎么着?”我看着他试探问。 盛大人没接茬儿,长叹一口气。 “您要是这么个败家法儿,就算是再生三个我这么能干的闺女,咱家家业也禁不起造。” 聊到这儿,我想起来,今天是嘉贵妃请脉的日子。 看着我爹这副样子,恐怕是有什么变数。 “圣人让官家给你指了一门婚事儿。”我爹捂着脑门儿,从牙缝里挤出费劲挤出这句。 这话一出,我登时僵住身体。 “谁家?”原本一车教训败家爹的话尽数噎在嗓子眼儿,只憋出两个字儿。 “安平侯家那个老二。”我爹一脸愁容。 一个月前,我爹负责照看的嘉贵妃突然有孕,可这一胎是不是喜事,那得看是对谁。 当今圣人被册封后位三年有余,一直无所出,嘉贵妃进宫不到半年,便传出喜讯。 皇室长子非嫡出,以后定是麻烦不断。 可是说破大天,这事也不该迁怒到我爹身上。 他进个医家本分,谁能想到把自己女儿——我也得搭进去。 这个时代,女儿家的终身大事就算是退一万步,也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对以后的婚事,我没憧憬过。 我管家这几年,府里的经济状况直线上升。 再也没出现过动辄就开库房当这当那换钱充门面的日子。 依照我爹原本的意思,他很可能会给我选个憨厚踏实的女婿。 让我这个顶梁柱能继续留在家里。 “能不能说我已经许了人家,已有婚约。”我端起桌子上茶碗递给他。 “那叫欺君。”我爹瞪着眼睛。“亏你想得出来,再说这个节骨眼儿,官家旨意已经下来,谁还敢上门给你议亲。” 得,这话当我没说。 “既然这样,那您躲在书房发愁也是无济于事。”我摆出一副任命的样子,“爹,您是不是担心我嫁出去之后,家里的日子不好过?” “胡说。”他重重拍下桌子,站起身扶手而立,“哪家的女儿像你这般跟父亲说话。” 被我直白戳破心事儿,我爹明显有些绷不住面子。 “你这个丫头,官家就算是把你指给阎王爷我也不用担心。”他一脸怒气看着我,“世子那副身子骨还能撑几年都不知道,你要是真落个孀居,爹爹肯定是要把你从王府讨回来,那时候再择佳婿也不迟。” 我爹算盘打得挺明白,可他哪里知道。 这门婚事儿属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安平侯世子林景熠,病都是装的。 3 发现林景熠装病这事,对我来说是无妄之灾。 我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安平侯府大门常年紧闭着。 因为不能开,只要一开就会往出掉放不下心眼子。 这话浅直,却足以说明,安平侯府就是京城的一片烟瘴林子。 一年前,老王爷打西北班师回朝。 除去皇城根儿的王府,官家还将京城西郊挨着百兽园的一处好大的宅子赏给王爷作为别院。 我第一次见林景熠,就是在哪儿的一次秋猎宴上。 宴会过半,我爹喝得烂醉如泥,医院的同僚从酒桌上驾到回到院中休息醒酒。 当时正值夏末,西郊草木繁盛。 我带着丫鬟子苓从女眷们扎堆攀比的局面上早早退下来,准备四处走走,看看周边有没有可以移植回家的罕见草药。 一不小心就溜到围场附近的山路上,遇上两个轻装简从的男人。 二人牵着马,见到我和子苓不由得微微一惊。 为首的人并未发话,眸光中透着戒备和审视。 随从的男子率先拱手向我行礼,提醒我们主仆二人此时围场中狩猎尚未结束,贸然靠近容易发生意外。 随从说话的同时,我无意间闻到为首男子身上散发着阵阵鲜血的腥味,可是并非人血。 我不想无端生事,当时就带着子苓识相的原路返回到宴会上了。 原本以为是个小插曲。 可没想到的是,在宴会的后半程。 一个时辰前刚刚见到轻装男子,眼下形容憔悴,似乎勉强撑着身体恭敬的端坐在安平侯家的主席上。 我和子苓面面相觑,正疑惑。 下手过来一个面生的小厮,说世子身体不适,想让我过去看看。 我让子苓留在原地,独自跟着来人,来到院中避暑的凉亭中。 林景熠瘫坐在藤椅上,身上盖着一件披风。 “世子的病,我可治不了。”我开门见山,“暑热天气这个捂法儿,恐怕得看看脑子。” 林景熠将躺椅掉个方向,背对着宴会厅,正对着我。 “你去围场后山干什么?”他盯着我的脸问。 “采药。”我大方的迎上他目光。“世子大人,您家里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也不想清楚,我爹什么德……什么情况,想必您应该有所耳闻,这就是个意外。” “盛大人医术高明。”林景熠似乎没想到我这么直接,反倒客气起来。 “我爹医术高明,可治不了您得病。”我继续说。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病?”林景熠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听到他这话,我当时只觉得两眼一黑,脚步虚浮,趁着感觉便装成中暑晕在当场。 我爹靠谱,看人却挺准。 当时我要是不装这出,姓林的不会这么轻易放过。 我本以为,对他,能躲就行。 他林家就算全家人都长袖善舞,反正也舞不到盛家院子里。 谁能料到,官家旨意,让这事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4 我很烦,烦这门婚事儿。 可更烦我爹。 古代婚姻流程繁琐,自从圣旨一下,林家人上门的脚步就从来没停过。 作为闺阁少女,我自然是避而不见。 可每次送走林府来人,我爹就会跑到我的院子里长吁短叹,捶胸顿足。 每次唠叨到动情处,老泪纵横。 刚开始感觉还行,听着他念叨起前尘往事。 佯装成思念我娘的样子,我还能顺着他的情绪装着安慰两句。 可是次数多了,我这人上辈子在急诊见惯生离死别,肝肠寸断。 说难听点儿,我是个铁石心肠。 在陪哭或是提供情绪价值这事上鞭长莫及。 好在我深知他是个烦心事不过夜的豁达人。 在我这儿这里哭完,他转身就能洗把脸出门去全京城最好的酒楼尝新酒。 这天林家人上门问名。 我爹依礼招待。 谢客后,他命小厮抬着两大箱子沉甸甸的东西往我住的院子里过来。 我害怕见他。 早就吩咐子苓要是爹爹再来,就说我昨天熬夜配药,现在正在打盹。 结果他老人家根本没把这番说辞放心上,直接无视子苓和另外一个小丫头,径直的闯进来。 “卿卿?” 我没想到他会硬闯,此时再往床上躺已然来不及。 情急之下看到面前茶盏里的半碗茶,便快速伸手沾上茶水,胡乱的抹在脸颊。 我背对着我爹,抬起胳膊,小心的擦拭着脸上的水渍。 可父女这么多年,我是个什么脾气秉性,他一清二楚。 这种临时起意的以泪洗面,根本就骗不过他。 “快拉到吧,装都装不像。”盛大人拂袖而立,无奈看着我,突然想到什么。 “这样不行,这哭,你得跟你姨娘学学。”盛大人一脸严肃,“这以后到了夫家,不会掉几个金豆子,博不来男人的怜爱。” 我听到这话,立刻抹干净脸上的假眼泪,登时狠狠白一眼我爹。 我爹苦着脸:“要知道你今天得落在他们家,我年轻时候多少也得给那小子他爹——林霆那泥腿子留点儿面子。” 5 这些陈年旧事,我在饭桌上听过不止一次。 老侯爷如今战功赫赫,可林家根基其实一点儿也不深。 安平侯父亲是草莽出身,老侯爷当年随父从军。 烧冷灶,烧出一个奉诏继位的旁支宗室子。 一人得道鸡犬飞升,林家也从边远之地举家迁往京城脚下,世袭安平侯。 一夜之间,林家成为京城新贵,林景熠的祖父去世后,爵位由长子林霆承袭。 自打林氏一族在京城站稳脚跟,我爹就看林霆不顺眼。 听说盛家祖上也做军医的当家人,曾经随王师征西。 可惜后世子孙都无意军功,到我爹这代,医术倒是没失传。 跟当时林家相比,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爹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纨绔,却一直稳坐京城美男的榜首, 直到安平侯林霆截胡了祖父给我爹早早看好媳妇儿人选——清河史家的嫡长女。 我爹彻底炸了,不分场合的各种大放厥词:“林家那小子是个什么东西,脚腕子上的泥还没洗干净,就敢跟我盛时珍争媳妇儿。” 这话传到我祖父耳朵里,换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嘴巴子,打得他耳鸣一个月。 自此,我爹就视安平侯林霆为眼中钉肉中刺。 逮着个机会就要埋汰两句,人家积极上进,军功卓越,他就说人家是利欲熏心,善于钻营之辈。 如今圣上一纸婚约,我嫁到林家属于前途未卜,他也只有烦闷的份儿。 “我看老侯爷也不是心胸狭窄之人,就算您筹谋再多,恐怕也是多此一举,眼前有比大生意,您过过目?”我起身走到书房的木案前,拿起几张药铺的进货单,递到他面前。 我爹接过仔细核对后一脸疑惑;“怎么一下子囤这么多货?还都是一些军中的常备药材?这么大的量,我们京城的几十家药铺就算半年也消耗不完吧。” “上个月我去定国公家的京郊别院赏菊听戏,听起国公夫人谈起要将女儿从定州接回来的议亲。” 我说着抬眼看看他。 定国公就这么一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 定州距离京城路途遥远,随行的队伍人数不少。 军中人身份敏感,不会在京城盘桓过久,趁着这次机会,定会大量采办一些军中常备物品。 “好家伙,这宗大生意下来……”我爹笑着竖起大拇指,可话却说到一半就咽了回去。 “这宗大生意下来后,够您折腾好一阵的?”我毫不顾忌的接过话茬儿。 “胡闹,你这说得什么话?” 我爹板起脸,伸手摸索着怀里掏出一张纸。 我接过定神一瞧,竟是三张写的满满的嫁妆单子。 “你娘当年的嫁妆,唯独有一副龙凤配我留下。”他说着低头长叹一声,“加上西郊的庄子,五处药园子,还有禁中赏下来的,连带林家的聘礼,你都一并带去吧。” 我着实没想到,盛大人这些年挥霍无度,府内每月开支如同流水。 娘留下的东西,竟是丝毫未动。 “怎么,嫌少?”我爹乜斜着眼睛。 “女儿不敢。”我佯装柔弱,小声道。 “你也别高兴的太早,侯府可比不得咱们家好料理,人多事杂,他们家老大的媳妇跟侯爷夫人一样,也是出身清河本地有名的清流世家,大婚时可真是十里红妆,你爹我可没那个本事。”他说着,不禁又是一声长叹。“你过去之后,得收收性子……” 他说着定睛看着我良久。 用一种很陌生严肃的审视眼神,只是一瞬,又无奈摇摇头。 他重新抬起头,目光中依旧透着慈爱,看向我。 “我知道你……不是她。”盛大人淡淡道。 …… 6 我霎时间身体僵住,不敢与他对视。 “卿卿?” 许是见我半晌没吭声儿,盛大人伸手敲敲我的脑门儿。 我回过神,哑然看着他。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脸上闪过一丝我这些年从未见过的悲伤神色。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努力适应这个身体和这里生活开始,便从来就没打算把这秘密说给任何一个人。 如今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向巧舌如簧的我也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应对。 “你莫多想……你那年大病一场,原本就是妙手回春如我也自知无力回天……” “您是如何察觉的?” 盛大人口气淡淡的,又换上刚刚进屋后那种玩世不恭的架势:“世间事本就无常,老天爷让我做一遭父女,天命如此啊……你自己若是难以启齿的也就不要去多想。” 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一番话如鲠在喉,不知道从何说起。 盛大人苦笑着摇摇头:“不管彼时你是谁,如今都是我盛府的嫡长女,” “有件事……女儿一直没有和爹爹言明。”我压低声音。 “哦?何事?”盛大人疑惑。 “安平侯府的林景熠,根本就没病。” 我将这事儿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全部道出。 盛大人沉默的思索半晌,恍然大悟的捋捋胡须:“这些年我也不是没怀疑过,只是侯府门禁森严,甚少在外寻医问诊,往深想,恐怕也是这个缘由。” 见我沉默一语未发,盛大人便起身在屋内踱步。 “唉,爹知道你打小儿就主意大,原本打算给你寻个憨厚老实能听得差遣的夫婿,家里的底子单薄些也无妨,可是圣上的旨意已成定局。”盛大人感叹。 我并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 或许他希望我撒个娇,像平时一样,板着脸不轻不重的揶揄回去一句半句。 他的怀疑也可以打消一大半。 可是往日里在他面前伶牙俐齿的我,却始终解释不出一个字了。 …… 晚饭期间,我闷头吃饭。 这几日,林家的聘礼单子在家里引起不小的波澜,两个姨娘更是每天扒在我爹跟前想尽办法打听我的嫁妆单子。 生怕我爹为在老侯爷面前充大个儿,陪送出去半个家底儿。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36%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ycxz/11719.html
- 上一篇文章: 技术对人的排斥之九研究者的价值被压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