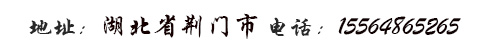广场白春日本ldquo乡居
|
今年四月至六月,我在日本住了两个多月。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是,以前去日本都是去旅游观光,饱览名胜古迹,东京大阪,京都奈良,乃至南部的福冈,行色匆匆,走马观花。而这一次却是驻足一地,饮食起居,完全是在日本的一个小镇上居家过日子。 这是因为,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变了:女儿考上了日本筑波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要在日本读书。而她的切身困难是,女儿年方四岁,腹中又怀上了二胎——当然是意外之喜。她要抢在生产之前,完成新生入学后第一个学期的学业,孩子无人照料,她自己也需要人来照顾。她的先生工作繁忙,脱身不得,而我恰好刚刚退休。如此一来,一个“光荣使命”就阴错阳差地落在我们老两口身上——陪同孕妇、带着外孙女,拖家带口,奔赴东瀛。 筑波这个地方,我从没来过,不过这个地名倒是很早就听说过。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天津的书画名家王学仲先生就曾多次跟我讲起他在日本筑波大学任教的情形,还送给我一册他在筑波出的书画集,使我把这个城市和这所大学记在了心里;九十年代初我迁居深圳之后,偏巧深圳与筑波结成了友好城市,我在报社工作时处理过有关筑波市的稿件。单凭这两条,就足以使我对这个日本新兴城市颇有好感。如今,女儿又来筑波大学读书,我暗暗觉得,似乎是与这个并不知名的城市,有着某种特殊的因缘,也未可知。 我们租住的是一套专门为筑波学子服务的居家公寓,类似于民宿。与筑波大学校区仅一街之隔,从住处去大学总部只需步行十几分钟,女儿去上课步行也只一刻钟左右。对于留学生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上佳的位置。但是,居家过日子却并不方便:附近没有菜市场,最近的超市步行也要20多分钟,且不通公交;交通出行也不是十分便捷,只有一两条公交线路可到“筑波中心站”,那是一个中转站;公交班车虽然很准时,但间隔很长,班次是随着乘客客流的多少而安排的,一旦错过一班,就要等上半天;还有一点,就是周边没有任何文化娱乐设施,也较少餐饮店,更不要说名胜旅游地了。那天,我和女儿抵达筑波,打的士找到住处时,已是暮色沉沉,收拾停当已近深夜。翌日晨起,推窗望去,竟然发现窗外正对着一片农田,土地已耕耘完毕,正待播种。我不由得对女儿嘟囔一句:“嘿,我们这回真是来日本‘上山下乡’来了。”女儿笑道:“可惜筑波山离这儿很远,我们也很难去。”我说,那就只剩“下乡”了。说罢,父女相视一笑。 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和号称“不夜城”的深圳,天车腾云般地飞赴东京,再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来到这个以教育和科技闻名于世的现代化大学城,初次与之亲密接触,目之所见身之所感,真是有些诧异有些不适也多少有些失望。就我的内心感受而言,可谓无聊又无趣,还要再加上几分无奈。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把公寓里备好的被褥席地一铺,把煤气灶下面小柜子里贮存的锅碗瓢盆菜刀砧板一一取出,心里自语道:“行,日本乡居生活,就此开启吧!” 学会采买 平生最欠缺的就是买东西的本事,活到花甲之年,唯一敢说会买的东西只有书。除了买书,我基本上没有单独买过任何东西。与此相应的是,平生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陪女人逛街,当初在深圳发现有家大商场专门开辟一块休息区,美其名曰“老公寄存处”,真是深得我心,还曾写篇小文大加赞赏。 孰料造化弄人,我此番来到日本陪读,被安排主管的事项竟然是每天去超市采买,包括买米买面买青菜,买鱼买肉买牛奶,举凡家中开伙做饭饮食起居日用之物,皆归我管。我曾支支吾吾想换个差事,毕竟买东西是我的“短板”呀,可是家里的两位“上司”——妻子和女儿也很客气,征询我的意见说,那您再看看眼前这些事儿,您能选哪一件:替我做饭行吗?不行;替我去上课行吗?也不行;专职带外孙女,这个活儿挺好的,您倒是没问题,可问问孩子行不行吧?外孙女立即大声喊道:不行不行——得,啥话也甭说了! 真没想到,从前在国内从不进商场,如今却跑到异国他乡来“专司”采买——拿着个手机导航,依照女儿的指点,我去寻找离家最近的超市,如同奔赴一个陌生的“战场”。走了约20分钟的路程,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字招牌——KASUMI,对,就是这个地方,一个24小时营业的食品超市。 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住所与超市之间,依照主厨的指令,采购过日子所必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最麻烦的是不懂日语,无法问询,只能凭着搜索的目光,扫描那一排排摆满商品的货架。幸好在日文中总会夹杂着一些汉字,让我不至于像大海捞针一样陷入迷宫。 开始那几天,我这个采买的学徒工确实交了一些学费,买来的东西主厨不甚满意,也有些东西买错了,货不对板。比如,“上司”中午要炒个醋溜土豆丝,一大早就发令让我去买醋,我不敢怠慢,疾步而行,到了超市,在货架上扫描数遍,都没看见标有“醋”字的商品,只好空着手回家复命。幸好女儿从网上搜出一个专营“中华食材”的小店,我赶紧颠颠儿地摸过去,终于买到一瓶正宗的山西老陈醋,这才算解了主厨的“燃眉之急”。还有一次让买瓶香油,我跑去买回一个外形很像国内香油的瓶子,商标上也标有一个“油”字。谁知做菜时才发现,那是一瓶蚝油。好在,蚝油也是有用之物,我亡羊补牢及时调整,立即买了一团生菜回来——蚝油生菜,本是广东人的家常菜,也是主厨的拿手好戏,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因为语言不通,购物交费就成了一道难题。人家售货员对顾客都挺客气,往往会跟你叽里呱啦说很多话,你却一句都听不懂,实在有些尴尬。我起初还假装听懂的样子,跟人家会意一笑,或者用小时候在电影里学会的那点日语,来上一句“哈衣”之类,但很快就发现这只会让对方更加诧异,索性不装了,也不笑了,直截了当指指计价器,照数目字交钱,这也省去了对方的许多客套话。 三五天过去,我的采买业务越来越娴熟,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对路了。有时虽无“上司”的指令,单凭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也能果断出手,买回一些计划外食材,受到了“上司”的赞赏。有一回,我看到超市里三文鱼很新鲜,而且价格不贵,就大胆超量购入,转天,同样的东西就涨了价。这件事不禁让妻女对我采买的判断力和决策力都刮目相看了。当然,最重要的褒奖还是来自小外孙女,她吃着姥姥做的香煎三文鱼,连说“欧意喜”(好吃)。姥姥告诉她这是姥爷从超市买来的,买了很多,管够!小家伙冲着我伸出一个大拇指——小外孙女的肯定无疑是对我的采买工作的最大奖赏。 春菊·春雨·春笋 在我以前的概念里,购物是最枯燥乏味的事情。但自从在日本专司采买之职后,天天不是跑超市,就是逛药妆店,慢慢的,我也发现了不少购物的乐趣。比如说:认字。 在日本超市里时常可见汉字,这让我既感到很亲切,又觉得挺有趣。有些汉字一望即知,比如“豆苗”,摆在货架上的东西确实就是豆苗,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这种情况很少,大部分标着汉字的货品与其本意相去甚远,比如“大根”,是指白萝卜,倒也十分形象;再如“椎茸”,是指香菇,就不那么形象了。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种形貌皆似茼蒿的野菜(对了,日本人把所有新鲜蔬菜都叫野菜),标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春菊”。而最具传神色彩的一个名字,要数“春雨”了——春雨是啥?就是中国人餐桌上常备的粉条。试想一下,把一束粉条下到滚开的水里,不是很有些春雨丝丝、飘洒而下的意味么?由此,我倒是很佩服古代日本人对汉字创造性引进和应用的本领。 一日,我在超市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棵新鲜的春笋,这是名副其实的当令食材。当时恰值阳春时节,正是春笋破土、新竹拔节的当口。我当即不问价格,买了一棵回家——能在异国他乡,吃到新鲜美味的春笋,岂不是福莫大焉! 或许真是机缘巧合,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在住家附近的一片森林里遛早——那是一片以柏树为主的大森林,叫做反町森林——那天走得远了些,一直走到树林的外缘,竟然看到这里蔓生着几丛野竹,散乱穿插在大树之间。我无意中走到跟前,又发现竹子下方分明冒出几株新笋,鲜嫩欲滴。我自幼生长在北方,从没见过野生竹笋的样子,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南方山民上山挖笋的镜头。真没想到,今天却在日本的乡间,与竹林和新笋意外相逢。我弯下腰欣赏着新笋上面那些细细的茸毛,不禁心生欢喜。过了几天,我再次来到竹林,想看看新笋们长多高了,却诧异地发现,一些竹笋已被连根斩断,有些笋子就被弃之一旁。显然,这片树林的管理者并不喜欢这些竹子,他们应该是有意识地剪除新笋,怕这些侵略性很强的新竹长大了,会侵占柏树们的阳光养分和地盘。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在树林管理者眼中,这蔓生的野笋应属“恶竹”了。 多数被砍倒的竹笋都在一米左右,也有几棵比较小。我从中挑了两棵还比较新鲜的带回家中,给“上司”“审看”。她剥开一看,说还挺新鲜。我跟她说起了竹林的见闻,她说,就这么砍了怪可惜的。哪天有空,我也跟你去瞧瞧。 又过了两天,我俩一道走进森林,沿着小路弯到树林尽头,找到了那几丛竹子。前几天被砍的竹笋,此时有的干瘪了,有的腐烂了。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就在那些干瘪腐烂的竹笋旁边,又冒出了几棵新笋,已长到一尺多高了。真是“一夜四出雷雨起,满林无数长龙孙。”(陆游句。长龙孙,竹笋别名。) 这回,我们不再顾忌,一人挖了一棵新笋,携归家中。当天晚上,那玉箨的清香就飘溢在我们的小屋里,令人难忘。 两个月后,我们在日本的乡居生活即将结束。临行前,我和妻子特意去了一趟森林,想再看看那几丛竹子,毕竟这段竹笋之缘给我们平淡的日子,增添过一抹亮色。不想,当我们找到那个地方却蓦然发现,那片“恶竹”已荡然无存了——我们与这片竹林和新笋的因缘也就此告终。 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更多精彩内容请儿童白颠疯如何确诊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xwgj/3635.html
- 上一篇文章: 子鼠的零食定风波middot暮春
- 下一篇文章: 祝允明草书曹植诗四首,豪纵奔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