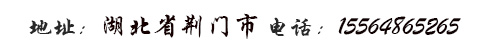在呜哇山歌的故乡
|
白癜风难治吗 http://pf.39.net/bdfyy/zjdy/190516/7143439.html雪峰山文化记得住乡愁 在呜哇山歌的故乡 ○楚木湘魂 我为草原村这个名字奇怪了很久。湘西南山里的村寨,或者叫岭,或者叫坳,相对平坦的一点地方叫湾。忽然冒出一个与“天苍苍,野茫茫”意象相关联的草原村来,就不能顺理成章了,就有点七颠八倒了。它是雪峰山系中的一个高原吗?它风吹草低见牛羊吗? 追究之下,它原来是叫蚂蝗村的,这个名字大概可以看出一点民生多艰的历史原貌。上世纪50年代,瑶汉两族村民响应号召,养猪牧牛,轰轰烈烈干了一场,于是就被叫成了草原村。它在隆回北部偏北处,在虎形山的山外山中,在云雾飘逸、山歌嘹亮的地方。 从大道入支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分支,路变成一条游蛇,时隐时没。山越来越深,绿色植物的气味越来越浓,暑气尽消,山风徐来,草原村未到,歌先来了。 (一)山歌 只蜜蜂飞过街, 丢了99只没回来呜哇呜哇, 还剩下一只长毛蜜蜂回来报个信, 一直飞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益阳汉口北京城内城外宝塔尖子上面脑壳溜起眼睛鼓起翅膀甩起爪子张起稀哩啪啦稀哩啪啦把信回呜哇呜哇。 最后一句一气呵成,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线钢丝抛入九天,在云中打着滚,滚到千沟万壑中,滚到苔藓覆盖的杉树皮屋顶上,滚到泛着粼粼白光的水田中,滚到密不透风的山坳里。 这就是久负盛名的花瑶呜哇山歌,它的前身是一种古老的劳动号子。在近乎原始的生产条件下,先民凭借肉体凡胎去征服自然,在陡峭的山体上一点点地锤出水田、菜园,种下苞谷、洋芋、糁子……唱歌的汉子在胸前挂上一面鼓,腰上吊只锣,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流星般地挥动鼓槌,胸腔里迸出穿云裂石的呜哇歌声,催赶着人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人们就在这血脉贲张的歌声中,伐木造屋,开山为土。 草原村是呜哇山歌的故乡。呜哇呜哇的男高音从草原村出发,随着先人迁徙的脚步,上了岭,下了坡,过了坳,走到了白水洞、大托、崇木凼,走进了溆浦县。歌在沟沟壑壑里冲撞,在起起伏伏的山尖上冲荡,在无尽的苍穹里奔跑,嵌入雪峰山系的骨骼,成为不可复制的民族特征。 我们顺着爬着苦瓜的篱笆,长着格桑花的阡陌,青蛙跳跃的小径,走到草原村的悬崖边上,选一个地方小心翼翼地站定,然后用手搭成喇叭,朝着峭壁下的白水洞喊:米兰,米兰,吃晌饭了么—— 米兰是一个很爱唱、也很会唱的女子,像一只伶俐的山雀,一个人就能把一个山谷唱得热热闹闹。白水洞不是洞,取其地势深洼之意,或许是“垌”的讹写。从草原村看白水洞,一目了然,你似乎能听到那里鸡鸣鸭叫,听到母亲呼唤孩子,看到炊烟袅袅升起。然而回娘家的女子从草原村走到白水洞,要磨烂一双新鞋。 草原村人当然也会唱歌,劳动、节日、婚嫁、迎客、敬酒等等,翻手唱晴,覆手唱雨,见景编词,不费吹灰之力,尤其以爱情为主题的最多。爱情是一罐蜂蜜,永远受着天上人间的恩宠。不受孔孟礼教束缚的高山之地,姑娘与意中人结成同“谋”,躲过周围的眼睛: 清早起来来会乖,莫穿白衣莫穿鞋, 假装出门看田水,顺着田坎妹屋来。 歌是沟通心灵的密码。你唱一句过来,我丢一句过去,对上了姑娘就跟你走咧!你开一个头,我接一个腔,对上了就是一个祖宗的后人。 歌是养生的粗粮,在人身体里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对抗风雨雷电、天灾人祸,庆祝生,悼念死,抚慰四时劳碌。 歌是一朵一朵的花儿,散落在树梢上、田埂上、堤坝上、水井里,再晦暗的日子也就明亮了。 远方来的客人被感染了,由聆听转入对唱,把喉咙放得很开,生命尽量向四周伸展,言笑晏晏,无拘无束。 美丽的花瑶女子娴熟地烤着苞谷,空气中升腾起了热乎乎的焦香,是一首物化的民歌。 (二)亘古的宁静 草原村太偏也太高了,山外的人难得进来,山外的东西更难得进来。山里人看着亘古的山峦,脉脉的流水,就沉淀了老庄的逍遥散漫。 绕过泉水脉脉的池塘,穿过万岁藤覆盖的石壁,就到了草原村的细湖凼。细湖凼尽头,是一处隘口。隘口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像一个巨大的蒲团,我们匍匐其上,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哦——呵——哦——呵——”声音被对面的山反弹回来,磕在石头上,轰然作响。 一整块石头就是一座山,或者一座山就是一整块石头,有的地方包着薄薄的土层,养育着飞刀剑草,直刺天空。有的地方就是一光到底的石壁,连苔藓也无法安身。我们把身子斜斜地放在石头上,脚下山风满谷,头顶寂寞满天,一切都叫人神俱静。工作的麻烦、谋生的艰难、孩子的教育、人与人之间的非议和揣测,都一一忘记。 眼前万物生长,生灵忙碌,野花自开。音乐家于无声处听有声,在这里寻找打动灵魂的声音。 青山重重,像惊涛拍岸。云生七色,无问西东,丹青手于气势恢宏中看到柔情,在这里寻找他们的画魂。 夕阳西下,织锦铺霞。摄影家于真实中看到梦幻,在这里捕捉可遇不可求的光影。 草原村的另一端,被机器拦腰切割过的石山上,形成一个阔大平整的平台。这真是一个干净得了无牵挂的世界。任流水漫过脚背、大鸟在头顶盘旋,醉鱼草香在崖畔上。石头那么大,比十个禾坪加起来还大。奔跑,跳跃,且歌且舞,应该是安全的,但步子总是不敢迈得太开,怕一不小心就绊在石头上,鼻青脸肿,怕一不小心被风吹落深崖,粉身碎骨。 眉眼清秀的小男孩问他妈妈:“西藏是什么?” “西藏就是天堂,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这里是西藏吗?” “对,这里是隆回的西藏。” 小男孩捧起小流瀑坠下的水来喝,又想起了一个问题:“水里从哪里来的?” “天上来的。” 村庄的女人从山里采来植物,挤出蓝色的汁液,将白布沉入其中,这是蓝染。清亮的河水倒映出女人们纯粹的笑容,映出她们健美的胳膊和腿,以及她们背后的蓝天白云。馥郁的颜色盛开在白布上,绽开了花,长出了草,勾勒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布晾晒之后,再经过女人们的巧手剪裁,就成了窗帘、裙子、头巾和客厅里的桌布。穿上这样的裙子,挂上这样的窗帘,就觉得自己在一段温暖的、点着檀香的时光里了。 草原村的七月很凉,当朝露未干,或者夜色徐来的时候更凉。不披一件长袖衫是抵抗不住这凉如水了。坐在呜哇山庄的旅馆里,在时光味、石头味、木头味、书本味的温柔包裹中,悠闲地睡觉、听雨、发呆、扯谈,看窗外月季颤动,黄牛低头吃草,蜜蜂嗡嗡地飞。 村落离天空很近,星子便觉得格外多,越看越多。数一数,歇一歇,自然是数不清的,也辨不出牛郎星和织女星,不过图一种趣味罢了。任远方声色犬马,我自安之若素! (三)通俗的幸福感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草原村的姑娘们常常去采野菜,或单独或结伴。春天采蕨芽、香椿、小笋、野艾。夏天采野蕌、紫苏、苦藤菜,总之每个季节都够她们忙碌的,契合了《诗经》意象。她们也把木槿花、丝瓜花、南瓜花掐下来入菜,显出一种把风雅烩入生活的情趣。 呜哇山庄的厨房里,呼呼燃烧的柴火,热烈地舔着灶壁,乌黑的铁锅烹出高山四季的味道,百合煨土鸡、小炒土猪肉、红薯叶尖儿,诸如此类,都是草原村发自内心的情意。丢几个洋芋、苞谷在火里,于是瑶家的姑娘和小哥哥,含嗔带笑地来灰堆中抢了。 木槿花汤可真是美呀!素白的花朵漂浮在碗里,像雅致的盆栽,撮入口中,丝滑清香,还没来得及咬,它就滑下喉咙去了。糁子粑在别处也吃过,但是甜味与红糖白糖都不一样,一问,用蜂蜜代替了糖的,怪不得一个碟子里伸出七双八双筷子的。 草原村的萝卜赫赫有名,它比山下的萝卜要脆、要甜,无论生吃、清炒、凉拌、炖牛肉、羊肉都是极好的,是素菜中的一个名角。有人特意走过千山万岭来了,什么也不要,就装一袋萝卜回去。但是我们没有赶上季节。 外面的世界太远了,出去一趟费时间又费钱,还特别折腾人。草原村的菜肴自给自足。猪栏牛栏,不让空置着,还有水库和池塘养了很多的鱼。水库又自带风情,吸引了许多人在此驻足流连。 大多数人家屋前都种着神仙叶树,每一棵树都显得阅历很深,能散发一种特殊的芳香,是隐形的防伪标志,因此容易识别。 七月,神仙叶长成。取叶子混和井水揉搓出汁,过滤去渣,拌入草灰水,汁液遇草灰水凝结成块,碧绿如玉,这便是神仙豆腐。调老坛酸水和剁辣椒而食,别有一种绿色风味。一家打神仙豆腐,左邻右舍都从家里拿了碗来,是味觉之外的另外一种趣味。 一层一层的苞谷地,苞谷刚刚黑了须。长在路边的鹅梨树,果实压弯了枝头。鹅梨树是原生的老树种,果子不大,但不需要服侍,年年数着节令开一树繁花,结满枝果子,它们已经适应自然,无需人力施以援手。山下嫁接的良种就不一样,不打药不施肥,就彻底萎顿了。玉米收下来之后,一部分喂了人,一部分喂了鸡,一部分磨成粉,掺入腊月的糍粑中,还是喂了人。 呜哇山庄主人一再强调,草原村的味道不是走马观花就能懂的,一定、一定要多住几天,你才能不辜负它。这话我当然懂。一碧万顷的绿色,乍看一眼,那就是山罢了。你一定要接触它、凝视它、抚摸它,才知道宏阔之中的细小,普通之中的美丽,单一之中的丰富。那些花、枝、叶,那些根和根养育的果,是一辈子都看不完猜不透的。你越专注,它就越神秘,越深奥。 一个村庄,乍看一眼,也就是木头房子多一些,泥土味重一些,风凉爽些罢了。一个民族,走马观花一看,只是服装和语言的差别罢了,唯有虚心静气,才能感觉到时间酿造出来的神秘与丰富,感受到自然造化的宽厚与温柔,才能感受到到处生命舒张的喜悦,才能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自适。如果人生果真能活得通透,如果生命能更多地接近地气,那么人生际遇所赐的悲苦,在灵魂安定的地方,总是能化解到最小,甚至于无。 感谢热爱这片热土的摄影人 摄影:雪峰摄影编辑:柴棚 邮箱: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yfyl/5329.html
- 上一篇文章: 武汉文学今日推荐青山依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