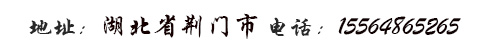莫家梁上5
|
小孩白癜风初期症状 http://m.39.net/pf/a_4791292.html莫家梁上。王宝顺家。这是一座典型的西北农家小院。黄土夯成的四方四正的庄廓墙,墙根很宽,墙上安着一个砖大门,门左边的对子早就没了,右边对子的字迹也被晒得白白的,大门两侧各栽一棵尖叶柳,水桶般粗。不远处,是一座楼式厕所,挂着草帘子。稍远处的猪圈上头盖着塑料布,有猪的“哼哼”声不时传来。进得院子,靠西头一溜四间松木旧房子,西南角里是两间伙房,北边有两间土担梁的小屋子。当院里,用胡墼垒起了一座四四方方的“中宫”,“中宫”里安着一个水泥墩墩,一座青砖雕成的小庙安在上头,里头有三盏铜灯。围着水泥墩墩还栽了好多花,牡丹、芍药、龙爪早已开败了,只有大丽花和菊花正旺得如火如荼。今天,这座庄廓里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反倒像过年一样地热闹。前来定亲的那伙人早就喝光了四瓶互助大曲,吃掉了炖猪肘子、酸辣里脊、油炸排骨、粉条炒猪肉、蘑菇炒羊肉等七八个菜。他们当中,有的人脸孔赛过鸡冠子,有的人面色铁青,还有的人脸皮白寡寡得像一张纸。他们越喝兴头越大,声调也越来越高,真有一副十八大碗不过岗的阵势。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一些从没摆过的东西:色彩艳丽的是衣料;黑皮鞋、红皮鞋、白凉鞋应有尽有;一只精巧的女式手表躺在衣料上,拇指盖大,秒针“嘀嘀嘀”地沿着规定的方向一圈又一圈,不慌不忙地走着。紧挨衣料的是两包益阳牌茯茶,一块正方形的羊肉方子上箍了一圈大红纸,两只酒瓶子的脖子也被红头绳拴着。除此之外,胭脂、粉盒、木梳、篦子、袜子、手镯等一切订婚用的大小物件堆了一堆。大概是因为换亲两免了的缘故吧,桌子上就是没有票票。要知道,平时人家里订婚票票可是最大头啊。一进门,花花没吭声,趁院子里没人她悄悄地溜进西房的另一头,躲在装满猪饲料的四条麻袋后头,她要弄明白这伙人到底想怎么样。大概有人打了个手势吧,西房里的吆喝声、吵闹声静了下来,只听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在屋里回荡,撞击人的耳膜:“我说宝顺哪,趁着大家都还没醉倒,就先把事情扯一扯。我看你也是快奔四十的人了,有啥主意还拿不定的?爹妈殁了,你就是米柜上的‘灶王爷——一家之主’,这事你说了算,要放干脆些,不要拉泥带水的。二柱那头嘛,早就打鼓着接神哩。今早临来之前我去了他家一趟,麻烦啊,他阿妈新近又添了病,看样子挨不过旧历年。一见我她就哭着央及,她说,二阿舅,你给宝顺求个情,下个话,紧事紧办,拿喜事给我冲冲病,兴许我能好哩,我实在丢不下这个阳世啊!我的意思是老人们的愿望当小辈子的最好甭违背,倘若老人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就会后悔一辈子的。”说这话的是李二柱的二阿舅,一个干巴但很利落的老头儿。抱头呆坐的宝顺听了老汉的话,抬头瞟他一眼仍没开腔,一张破板凳被他扭得“吱吱扭扭”响。“哼,做梦娶媳妇——尽想美事!”这边,花花愤愤地从心底里骂了一句。背靠门箱歪坐着的是李二柱的姨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弹弹烟灰,拔正身子,接上了话茬,说:“我说宝顺同志哟,人不是常说凡事都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嘛。像娶媳妇这号事更得紧上加紧,最忌讳拖拖拉拉,要快刀斩乱麻,夜长梦多啊。这么的样样不少了。远处的暂且不说,单就你们莫家梁这几年一连就出了三桩麻烦事。你们下社里张背篼家的喜喜、上巷子里窦家的桂桂、你隔壁赵铁匠家的玉芳,本来说得好好的同意换亲,结果临到喜日子了,你看,抹脖子的抹脖子,吊麻绳的吊麻绳,喝农药的喝农药。再不,就跟上个外来人神不知鬼不晓‘鞋底子上抹油——溜了’,管球你两家鸡飞蛋打。”听到这里,宝顺的身子微微抖了几下,呆滞的眼神停留在墙上那黄塌塌的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照片上,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神态若有所思。“可不!”炕头上盘腿坐着的媒人,一个四十来岁的细高个儿女人手里攥着一条鸡大腿,边啃边说,“我说宝顺哪,二柱的大妹子实话是花儿里头的白牡丹,马伙里的走马,人伙里的人尖尖。”她撕下一大块鸡皮塞进嘴里嚼几下囫囵半片地吞下肚,又开了口,“你看她平日甭出门还罢了,一出门,尻子后头尕小伙儿一帮一伙的,零花钱、衣裳、日常用品,家里从来没为她操心过。”“二姨娘,你胡谝哩,我妹子哪是那号人,说话把住点儿,也不怕闪了舌头。”李二柱急眼了,他怕二姨娘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搅黄了换亲的事。“哟哟哟,看我这张破老鸹嘴尽胡诌哩。我也没啥坏心,只是想在宝顺面前夸夸你的妹子呗,其实她稳当得很哪。”她讪讪地一笑,忙给自己打圆场。她又接上说,“宝顺哪,一定要抓紧哟。倘你不抓紧,万一叫外旁人恋上、爱上啥的,那就狗咬尿脬空欢喜了。现如今只认钱,不认人的这个世道里啥怪事都有,尤其大姑娘的心就更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阴晴不定哪。”“对着哩,对着哩,半点儿都没错!”媒人的话音刚落,来订婚的人齐声附和。宝顺转过脸瞅了媒人一眼,心里骂道:“球!啥人伙伙里的人尖尖!一个克死了俩男人,瞎了左眼的二婚头,还带着一个尕丫头,我前几十天就见过。凭她的那份人才给花花端屎倒尿都不配,还传啥人尖尖哩。”骂罢了,他沉下脸仍不表态,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烟头满地都是。黑暗中,花花气得浑身打颤,想:“这帮长舌头,原来就是这么撺掇老实人的。既然事情紧,李二柱的妈妈病重,那就把你们家的丫头、媳妇娶给去呀!”她愤然站起来,要进屋论个长短。就在这时,忽听宝顺喊了一声:“亲戚们——”她只好又原地蹲下。电灯泡的光亮里,只见刚才还蔫不唧儿的宝顺掂量了一阵大家的话后,态度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的眼神变得明亮起来,精神也振作了。八成,他是叫这伙人的海吹胡擂涨昏了头脑,也许可能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吧。他望望这个,瞅瞅那个,最后一拍大腿,说:“中!中!听了老人言,一辈辈不受难。二柱——”他扭过身子,叫一声,“我同意换。但是丑话撂前头,我妹子俊,你妹子丑,你得给我妹子找点儿钱。‘麻眼儿打平伙——公道要紧。’我也不想多要,你就找给五万块吧,我也好给花花说,少一分就拉倒!”李二柱不干了。他拧歪了脖子说:“这话你就差了去了。我们俩这是‘鸡蛋换线——两不见钱’的买卖,一个囫囵人换一个囫囵人。你我妹子的脸都是一块板板儿,七个眼眼儿,谁都没多长个啥东西,只不过胖瘦不一样罢了,凭啥要我找钱呢?”“就是,就是,二柱说得有道理。你们两家是‘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只要婚后俩人攒劲干,还怕没钱吗?钱呗,它本就是人身上的垢痂,洗掉一层有一层哩。宝顺,既然大事成了,就甭在这点上计较了。”来订婚的人们又一齐劝道。思谋了一阵,宝顺脸上又放晴了。“那成吧。反正也就这么回事了。明儿我先去‘神树’前点个香,再找焦巴儿算个日子,趁早把事儿办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妹子丑,我妹子俊,总觉得吃老亏了。”宝顺似乎一脸的冤枉。“对啊,对啊。这么说我俩想一搭里去了。这叫啥来着?哈哈,照书本本上讲,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按庄稼人的话就是‘曹操碰上蒋干了,瞌睡遇上枕头了’。放的干干脆脆的事不办,拉泥带水,费那么多气力干球哩嘛。”李二柱拔下叼在嘴上的纸烟,掐灭了撂地上,捏得指头骨节“嘎巴嘎巴”响。看他那副猴急样,恨不得今晚上就当新郎入洞房。“我说还是宝顺干散,钉是钉,铆是铆,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活人就该这样。唯唯诺诺,婆婆妈妈的人我一见就翻黑血哩。来,二柱,快给你宝顺哥看上四盅酒,人逢喜事精神爽,四红四喜满满上!”干巴老头儿一发令,炕上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跪起来,满盈盈的四大盅酒立时摆在宝顺面前。宝顺憨憨地、开心地笑笑,舌头贪婪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干哪,快干哪,办事干散,喝酒也要干散哪!”大家伙齐声撺掇。宝顺用三个指头撮起酒杯,刚凑到嘴边但很快又移开来,他又没了方才的豪爽,神情显得沮丧,迟疑起来。他放下酒盅,走到房门口扳住门框往外张望,外头很黑很黑,啥都不见,只听得“呼呼”的风声。宝顺折转身,略略沉思一会儿,又端起酒盅,手却“唰唰”地抖,怎么也放不到嘴边,他只好再次把酒盅放到炕桌上,自嘲地说:“你看,你看,我这记性叫狗吃了。花花属小龙,满打满算今年才吃了19岁的饭,要早点儿办结婚证可领不上啊。”他又坐回破板凳上,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宝顺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浇灭了满屋子人们心头喜悦的火焰。大家你看着我,我瞅着你,“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了。是啊,这确实是个要命的事情,不到结婚年龄硬结婚,那可是太岁头上动土的事,违反了婚姻政策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立时,屋里除了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气声和“嘘溜嘘溜”的喝茶声外,再没有了别的声音。黑暗里,花花暗暗松了一口气,心也稍稍宽展了些。她心里说:“哼,你牛再大,还有个治牛的办法哩。没有结婚证你就跟风结去吧。”此刻,她真想放声大笑,出一出憋在心里的闷气和惆怅。但她没有。……“嗨,看你们该愁的不愁,偏愁晴天里没日头。”就在沉闷得十分难受的时候,一直蹲在长板凳上抠脚丫的李二柱噌地跳下来,把半截冒着青烟的烟巴巴往茶碗里狠狠一按,套上皮鞋,晃晃脑袋,变戏法般掏出两个红本本很得意地撂在炕桌上,说,“嘻嘻,宝顺大哥,你熬煎个球哩。如今这世道哇,我算是‘碟子里舀清水——看透了’。你不管办个啥事,都得讲究个门路,讲究个关系,讲究个人情。说穿了,一要大把大把地花钱,人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照我看钱多还能叫磨推鬼哩。二要抓住当官人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把柄,啥事就都能办成。当然了,当官人见不得人的把柄不是你想抓就能抓到的,这得碰运气。没娘的娃娃天照顾。嘿嘿,这回偏偏就叫我这瞎牛碰上草坡了。妈妈的,这结婚证整得也实在太容易了,倘若在座的愿意听,我倒想谝一谝哩。”李二柱打住了。他十分炫耀地望着大家,顺手再抽支烟噙在嘴上。“快,谝谝,我们这些老半死们也学着点儿,往后娃们办点儿事说不定用得上呢。”大伙儿缓过神儿来,齐声嚷嚷。黑暗里,花花着实吓了一大跳,立刻全身发冷、发抖。她拿脊背抵住麻袋,屏声敛气,细听起来。“好咧,那你们就把耳朵奓起来吧。”李二柱抿口茶,润润嗓子,说,“其实,换亲这事我跟宝顺哥早就说妥了。说妥以后哇,我心里反倒添了一个病,因为凭我这副猪八戒样样,凭家里跟解放前没啥两样的穷劲道,要娶花骨朵般的花花,那简直和猴儿捞月亮没啥两样。那咋个办呢?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呗。我就慢慢地琢磨,无论如何首先要把结婚证搞到手,因为它是命根根,只要把它搞到手,天王老子都干涉不着。我就想呵想——”李二柱卖了个关子,趁势喝了一大口茶。“快接着说,接着说。”大伙儿又催。“嗬,到底给我想起来了。乡政府的马乡长正好是我二娘娘的一个远房姑舅,十多年前走后门吃上了皇粮。早就听人说,这家伙溜尻拍马,很不得人心,大前年不知怎么还就当上了乡长,牛皮哄哄得很。我还听说他是个‘酒盅盅一端,政策放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尕便宜上要紧死哩,给人批庄廓、定低保、发救济啥的从没按政策办过,当地老百姓就怕他不早死。我高兴了。球,就在这个有缝缝的鸡蛋上下它个蛆儿。人常说‘小恩惠能买转帝王的心’,更何况他还是个凡胎,是一个比凡胎还凡胎的凡胎。于是,我隔三差五就往乡政府跑,跟他套近乎、攀亲戚、送酒买烟。今年四月头上,马乡长要在乡政府旁边盖一个专卖水泥的铺子,我就豁上命给他明昼赶夜地干了六天活儿,饭自个儿吃,工钱一分没要,把他美得要死,平日里一照面一口一个李尕兄。一天中午里,我没事又去找他。乡政府院子里安静得很,一楼、二楼所有的门上都吊着铁猴儿,只有三楼左手第三间的门半掩着,里头有吱哩哇啦的声音,我就三七没管二十一一把推开了门。天哪!我浑身的血都不淌了,头涨得有背篼大。你们说,我看见了啥?他妈妈的,马乡长正把一个他的朋友的年轻媳妇压在席梦思床上拽裤带哩。我能不慌吗?我连忙说,没见,没见,我啥都没见,你们忙,你们忙,然后就一溜烟跑回了家,头里晕晕乎乎的,半后晌不知该干啥。”“这个狗日的,还是乡长呢,真丢共产党的脸。不如个畜生!”大伙儿愤愤不平地骂起来。“后来怎么样了?”干巴老头儿问。李二柱续上话茬:“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吧,马尿雨儿‘哗哗哗’往下倒着,姓马的开着乡上的桑塔纳,提着两瓶五粮液、两条软中华来了。他一进门就央求说,‘李哥,下话了,实话下话了。那天的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万千万给保个密,我一个庄稼娃娃能混到今天这个位子确实也不容易哟,这个饭碗踢掉不得。只要你给我守住了这个秘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往后只要你说打男的,我决不会揍女人,有啥难处尽管言传一声。’嘿嘿,就这样我把结婚证顺顺当当搞到手了,年龄限制算个球哇。人呐,一旦时运顺了,插根扁担都能开花哩。哼,有了它,我还怕他马王爷长着三只眼吗?”“那花花和宝顺的相片你是咋弄上的呢?不到年龄硬结婚到底中不中哪?”有人插了一句。“高人自有妙计。那回我把宝顺哥整醉了,从他家相框里拿的呗。至于她的年龄嘛,我不急,四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个四五年没啥问题。”李二柱大大咧咧地说。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房里立刻就像降临了喜神,大伙儿原本紧绷的面孔一下松弛了,个个喜笑颜开,伸手抢那两个红本本。还是宝顺眼疾手快,他用宽厚的脊背挡住伸过来的手抢先把结婚证抓在手中,急忙凑到鼻尖尖上详详细细地瞅。猛地,他满脸的喜气顿时烟消云散,换上的是一片愤怒和羞辱,拿结婚证的手也索索地抖个不停。毫不含糊,王宝顺,这个在小学蹲了八年将就着能认得自己名字的人这回看清楚了结婚证上只有“李二柱”“王花花”两个人的名字,与他竟毫无相干!隐隐地,他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眼里喷射出两道愤怒的光亮,牙缝里硬铮铮地挤出了“狗日的”三个字,动作也变得粗野起来。“咚!”他一拳砸在炕桌上,三四个大碗一跳老高,然后又“丁零当啷”摔下来碎了两个,汤汤水水洒了一桌子。宝顺气急败坏,指着李二柱的鼻尖骂:“李二柱,你这个狗日的瞎货,使尖耍滑日弄到我头上来了。少客气,不见兔儿不放鹰哪。你为啥光给自己领结婚证,不给我开?你‘扁担上睡觉——想得宽’。哼,我王宝顺蠢是蠢,但这点儿灵性还没叫狗吃掉。今儿大家都有,我就把丑话说前头,喜事要办,两家都办;不办,一齐拉倒,你当你的光棍,我做我的独身。从今以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宝顺一口气说完,拉着脸就不理人了。大伙儿又沉默了。黑暗里,花花又轻轻地舒了口气,那颗近乎绝望的心又活了。她挪挪肩膀,揉揉酸麻酸麻的双脚。静了片刻,还是李二柱打破了难堪的僵局,他揪了揪肿汪汪的眼皮,耍魔术般地又将两个红本本扔到炕桌上,鄙视地冲宝顺嚷道:“你怕啥?去打听打听,我李二柱从爬出娘胎那天起,啥时干过过河拆桥的缺德事?前晚上我一家伙赢了前沟牛粉条匠的八百块钱,不就又分给了他一半?宝顺哥,甭慌甭忙,气儿悠长,详细瞅瞅这两个红本本上写着谁的名字。”李二柱撇撇嘴,斜睨一眼气急败坏的宝顺,满脸阴阳怪气。他再拈支烟墩几下,划根火柴点上,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宝顺狐疑地抬头望了李二柱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寻找。“快看看哪。”李二柱见宝顺不像方才那样激动,便努努嘴,催促他一声。宝顺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搔搔黑白相间的鬓角,拿起红本本漫不经心地溜……渐渐地,他那张灰不喇唧的脸上显露出喜悦的光亮。这回他看清楚了,红本本上分分明明地有“王宝顺”“李淑兰”两个人的名字,印章血红血红的。“咳,你实话是个胡日鬼。早点儿拿出来不就得了,干枉枉挨了一顿臭骂,划来不?”干巴老头儿笑着埋怨道。“我就是要故意惹惹他,看他究竟是啥态度。骂,由他骂去,打是亲,骂是爱,只要他嘴不困。”李二柱满不在乎。此刻的宝顺从心眼里舒坦了。他捧着红本本眉开眼笑,美美地擂了二柱一拳,说:“中,中。二柱,你这个干沟里有名的胡日鬼,今儿我算服了。”他侧转身朝着大伙儿高声道,“说定了,事情就这么办,操紧来快。我王宝顺如果再变卦,就不是人养的!”李二柱眯着眼笑了,脖子一仰,一大盅酒下肚了。满房房的人都笑了,白瓷酒盅又给宝顺端上来满满的、亮亮的四大盅。猜拳声比先前还响:“二喜临门哪!”“四红四喜啊!”…… 作者简介: 曹启章,男,生于年,青海湟中人,湟中区作家协会顾问,历任中共湟中区委宣传部部长、《海东报》社社长、《西海农民报》总编辑和社长。年起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文集《岁月的记忆》《足迹》,主编《油菜花飘香的地方》《圣域》《河湟涛声》等多部散文集,创作电视专题片《沃土》《宗喀巴大师的故乡》等。 西宁市湟中区作家协会 来源:《湟中文学》(小说卷) 监制:马彪 责编:郭成良 编辑:赵萍刘丽丽 精彩推荐第六十回袁大仙流芳百世梅花鹿受命归天仁青家的故事鸡换子莫家梁上(1)莫家梁上(2)莫家梁上(3)莫家梁上(4)扫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yfyl/5484.html
- 上一篇文章: 粉丝福利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的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