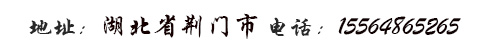井石中篇小说金凤蛋传奇
|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传递健康和希望 http://m.39.net/pf/a_4892467.html昆仑文学 KUNLUNWENXUE 微刊 第31期(总第期) 人生百象本栏不厚名家,不薄新人,唯优取稿金凤蛋传奇 中篇小说文/井石 好一个钱字了得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八十年代初,整个马营的人在一个早上个个如景丰山做了金风下蛋的好梦,喜笑颜开起来。原来这一天是生产队分地的日子,土地要承包到户了。 人一高兴天眼开,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一年,全庄子就夺了个大丰收。庄稼人竟然不相信,自己家没有能装得下当年收获的粮食的家什。面柜满了,泥仓满了,台基上也堆满了,场面上的碌碡还没滚罢! 这不就是庄稼人盼了几十年盼来的吗?生活呵!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如为寻找一条吃饭的路,饿了几十年;简单如他们一旦把土地掌握在自己手心里,就如变魔术般一夜吃了个肚儿圆。 人心没有鸡蛋大,骑上骡子想走马。刚吃了几天饱肚子的庄稼人,存在直肠里的榆皮渣子还没拉干净,就发现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黑,身上穿的衣服站不到人前头去,还发现城里人在听录音机看电视呢! 广播匣子里传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活时,一阵骚动的潜流刹那间如大潮,从每一个本来老实巴交的庄户人的心头上沉沉地压过。当庄稼人再回过头来时,全变了脸色。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这“一部分人”中的一分子。对钱的欲望如吹胀的猪尿脬,一下子把庄稼汉那空落落的胸腔填得满满实实,使他们浑身不自在。被窝里如钻满了青稞大的虱子,睡觉不得安宁,吃饭辨不出香臭了。 钱,钱,钱,钱在哪里呢? 整个马营的人疯了般涌出庄子找钱去了。回来时,也有几个多少挣上了点的,但大多数空手而归。 他们不知道怎样挣钱。他们卖力气也找不到地方。 不知是哪个老先人的机灵后人。先觉悟了,西部,西部有黄金!而淘金热刮进马营时,马上决定要走金场的不是景丰山,而是灶保姐的两个儿子,家龙和家虎。 家龙和家虎如今都成人了,一个28岁,一个25岁。家龙人老实,肯吃苦,如他老子刘广才。而家虎却是个鬼精灵,心眼儿活、歪主意多。弟兄俩相加在一起,一个出点子,一个出力气,配合得非常默契。 小时候,他俩最敬重的人除了自己的母亲,就是那位被人称之为金疯子的姑夫。只要几天不见姑夫面,他们就哭闹不止。要母亲把姑夫找回来。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俩慢慢发现了姑夫与母亲间不明不白的关系。特别是有一次,有个和家虎一样大的孩子打架时打不过家虎,竟骂他是金疯子的野种,气得家虎差点把那个孩子打了个半死。 从此后,家龙家虎一见景丰山到他们家来,就恨不得拿把菜刀剁了他,但当着母亲的面,又不好发作。他俩立下誓言,长大后,要设法弄死金疯子,为父雪耻。 老景丰山和老灶保姐发觉孩子们注意到了自己的行为。老灶保姐说:“怕啥哩,没有你深更半夜给他们偷洋芋吃,这两个鬼能长大?” “算了,你的两个姑娘出嫁了,两个娃娃也抵挡了,他们还要活人哩,还能把被窝里的事摊到日头底下晒?骚不拉几的。” 景丰山斜眼看灶保姐,做了个鬼脸。 “金疯子!谁骚了?你个皮嘴没好话。”灶保姐捣了景丰山一指头,“骚也是你先骚的。” “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身。”景丰山又斜了灶保姐一眼。 “好哇好哇,你个金疯子,我给你连儿子养了,你个没天良的贼。”灶保姐翻起身,绰起扫炕笤帚,在景丰山的大腿上美美一笤帚。 就在这年年初的一天,家龙家虎都出去劳动了。景丰山又瞅空钻进了灶保姐家。 两个老冤家凑到一起,陈年老麦子的话也多,三喧四不喧,忘了已过晌午,家龙家虎回来了。 灶保姐听着儿子的脚步声,忙了,她急中生智,朝窗子大声说:“他姑夫,有钱还不借给你吗?前一天青盐断了,没钱儿称,还从上院里借了一茶碗哩。”说完又使了个眼色。 “那就算了,我再想个办法,不抓个尕猪娃也不成,抓吧,又没一大钱儿,唉!”景丰山说着走出门。 “姑夫,你们家已经养了三头猪,娘娘成天喊没食喂要卖掉一头,你咋反而要买猪?” 景丰山脸就红了,这个家虎,似笑非笑,呛人哩。景丰山像小偷刚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就被一双犀利的眼睛盯住了一般,尴尬而又悲哀地立在那里。 “阿妈,人家们饿得瘪了肚子,你也不知道干了些啥,连饭没做!” 家虎扔下景丰山,进房门大声地埋怨起妈妈来,并把上衣脱下来摔在炕墙上,炕墙上立马扬起一阵尘土。 “这个娃娃,大了大了的,一点规矩也不懂了。他姑夫,你走,我就不送了。”灶保姐端了面升子,进了厨房。 “我不懂规矩?规矩是个啥东西?我要懂规矩,就不干让人戳脊粱的事,哼!” “算了家虎,少说两句吧,我的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条大狼狗,明儿个我拉来,往大门上一拴,啥事也没有了。”家龙拍了拍家虎的肩膀,提起铁锨,往猪圈里撂土去了。 打那以后,景丰山就很少到灶保姐家去了。好在家龙家虎都能抵挡一面了,那个家,再也用不着景丰山去费心操持了。 倒是灶保姐找尕麻娘铰鞋样儿、寻针借线的机会多了。 尕麻娘有理不打上门客,心里虽藏了一百个厌,但脸上还是装着笑儿。 “唉。也不知前世里造了啥孽,我这一辈子早晚要被这个骚皮皮气死!” 晚上,尕麻娘对斜靠在被子上抽烟的景丰山说。 “你呀,就算我年轻时把你亏下了,没对起,如今岁数一大把了,还阴阴阳阳地说那些儿酸话干啥?” “好,我垂说,这几十年,你明里一股股,暗里一股股地往那个皮脸不要的骚皮皮家弄东西,现如今人家的儿子大了,用不着你了,可你不看看我们这个家,你进来几十年,给我连光鲜点的一件汗褟没买过不说,三间大房变成了两间!墙上的口子见星星哩,满墙缝的雀儿窝,你如今叫你拉扯大的那个野种来拾掇拾掇呀!” “你说了半盆盆屁话!” “你才说了一辈子屁话!你不是看下瓜子儿金着吗?啊?你个不要人脸的老东西,现如今上庄下庄的人都奔着金场去了,你咋反而连个悄悄屁儿也放不出来了r景丰山张了半天嘴。又合上了。 终于当了金掌柜尕麻娘从菜园子里拔了两个红头萝卜出来,准备回家烧晚饭。景丰山在补菜园子的石头墙,不知谁家的捣蛋鬼进园子偷萝卜,扒翻了墙上的几块石头,烂了个豁豁,不堵上,保不住猪儿羊儿钻进去糟踏。 “姑夫,你干啥呢?”景丰山低着头一边抬石头,一边说“垒墙。”说完觉着不对,赶紧抬起头,愣住了,站在他前面,笑嘻嘻地问他的,竟是往日见了他,吹胡子瞪眼的家虎和家龙。 “哟,家虎……”景丰山把石头放到墙上,将两只沾满土的手来回搓了几下,诧异地看着对他亲热异常的两个冤家,又看看太阳,觉着今天天气正常。景丰山不知该说什么。 好一个钱字了得(2) “姑夫,往后有啥活喊一声,我和哥哥谁过来还不干了?”家虎抽出一根纸烟,递给景丰山。 景丰山激动了,他嗳嗳暖一迭声应着,伸出双手接过家虎递过来的烟,脸上竟出现了受尽欺凌的奴才突然得到主子恩宠后的不知所措来。 他将这两个小祖宗让进家,让上炕,又叫老伴儿倒了茶,拾上馍馍,自己却不知站着好,还是坐着好。好像他是前些年受管制的四类分子,炕上坐的是村支书和治保主任一样。 还是家龙起身,一把将景丰山拉上了炕头。 “姑夫,小时候听你老人家讲,解放前你当砂娃看下了一窝瓜子金?”家龙问。 “就是。全是瓜子金,我拣都拣了,可人们不信。”景丰山说。 “我们信!”家虎说。 “实话?”景丰山眼中放出光来。 “那当然,姑夫说的话就不可能有假。可是姑夫,你盼当金掌柜盼了一辈子,如今能当了,咋反而没听你有啥动静?四乡八邻的人都进金场了,就剩下我们庄子没动,人们都看你哩。”家龙说。 “看我?看我干啥?”景丰山问。 “你想,你是老把式,又是看下好金窝子的人,你都不动.旁人生路生手,敢动弹呀!” “嗨嗨。”景丰山高兴起来了,“那是,挖金子不像种庄稼,规矩海了去了,犯了规矩有金子也不出来。” “你就不想当一次金掌柜发他一回财?” “都这一把年岁了,人家孟牛头当金掌柜才40多岁。再说,金掌柜是有钱汉当的……” “哎呀姑夫,你错了!你身子骨这么壮实,比40岁的人还年轻,当金掌柜又不出力气。没有钱怕啥?如今政府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信用社动员人贷款呢!先贷了款干,挖了金子还账,这么便宜的事往哪儿寻去!”家龙说。 “噢?”景丰山伸长了脖子。 “贷了款,雇他二三十个人,再雇一辆卡车,你坐在驾驶室里指路,我和哥哥给你当拿事,挖他一两个月出来,你拿金子,我们拿工资,不都发财了?一发财回来,哥,我们先帮姑夫把这两间早晚要塌的破房子拆了,阔阔气气给姑夫盖上七间大房,你说中不?” “那没说的,姑夫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姑夫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连这么点孝心都没有,我们小时候白吃姑夫背来的干馍馍了。”家龙说。 家龙家虎的一席话说得景丰山眼里湿湿的,他一拍大腿:“走!我当了一辈子金疯子,天每日想挖金子发大财,临到头上,咋反而没你们灵醒了?家龙家虎,你们俩张罗这个事,我去乡上信用社贷款,我就不信金掌柜不是人当的!” 家龙家虎齐声道一个“好!”家虎又说:“姑夫的‘金凤蛋’该出世了。” 景丰山这就想起他一气之下扔进茅厕坑里的那个给了他无数个金凤生蛋之梦的石枕头来。等家龙家虎走后,他立即拿了铁锨进茅厕坑,把那个石枕头挖了出来,抱出门去,在水沟里洗干净了,又抱回了家。 “你实话要去金场?”尕麻娘把汤端到炕桌上问。 “我从17岁就梦这一天哩。” “你一把老骨头了,还张狂个啥?我们又没有个儿女,这两间破房子能陪到我们死。” “你那个舌头没脊梁,满嘴翻巴浪,前几天还骂我没拾掇这两间房子,说‘上庄下庄的人都奔金场了,你咋反倒连个屁不放了’,今儿又说我张狂,天底下的瞎话全叫你喷出来了!” “我那不是气头上说的气话吗,你倒拿上棒槌当针认,我看你呀,为你的那个野种儿子操心哩!” “你个死婆娘,我就是有个野种儿子,靠你,要叫我当绝户头!” “你如今还是个绝户头!这是你景家人缺德缺的!你以为你的那个野种真孝敬你哩,你甭高兴,人家姓刘,你姓景的瞪眼儿抻腿的那一天,连张纸不给你烧!” “唉哟老祖宗,几天没挨打,你皮子胀了呀你!我绝户了你光荣?是你老子先绝的户才招了我进来的,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不坐胎的母骡子!” 尕麻娘忽一下扑上去,打翻了景丰山吃饭的碗,于是,两个老冤家又像两只鸡,打斗了起来。 那天晚上,景丰山又一次枕了那个石枕头睡觉,朦胧中,那只金凤凰又飞来了,先是朝景丰山翩翩起舞,而后,一撅屁股,“扑通”一声,给他生了一枚金蛋,金蛋落地,发出清脆的金属敲击声,悦耳极了。 尕麻娘因和景丰山赌着气,早上起来,只管喂猪放鸡扫院子,却不烧早饭,连每天一早都要给景丰山的一茶罐茶也没给炖。 景丰山只是不吭气。他把那个石枕头拿出院放在花园墙上,先用桑熏,而后又拿进屋放到供桌上,又是上香又是点灯,末了,规规矩矩地朝石头嗑了三个头。 尕麻娘再看景丰山时,景丰山已出了大门。尕麻娘把大门哐当一声关死,想了想,又打开来,她感到委曲,就流起泪来。 景丰山大步流星地来到灶保姐家。他的这一次造访得到了家龙家虎的热烈欢迎,他们满脸是笑地把他让到上炕里,又是递烟,又是点火,景丰山只管老子样领受了。 灶保姐一看儿子们高兴,胆子也大了起来,蹬着鼻子上脸,飞进灶火,为景丰山打了四个荷包蛋,又放了一把芫荽,热腾腾端进来。景丰山也不客气,接在手中,如秋风扫落叶,三两下吞进肚里。灶保姐又炖了一茶罐好茶,酽酽地倒给景丰山喝。景丰山看见那茶碗里漂着两个胀圆了肚子的红枣儿。 “雇汽车雇砂娃弄吃喝,要多少钱,我心里没有个准数儿,你俩帮我算算。”景丰山一边嘘溜溜地喝滚烫的茶,一边说。 家虎说:“昨晚夕我和哥哥算了一下,连砂娃的工资盘进去,最多一万二就够了。 “那么多?”景丰山失声叫了起来。 “一万二不多,要是挖上瓜子儿金,8万也挣上了。”家龙说。 “对着哩,就怕……”景丰山缩了脖子。 “姑夫,你到底看下金窝子了没有?”家虎问。 “看你这个话问的,我这么大岁数了,还骗你们娃娃?”景丰山又急眼了。 “那就对了,实际上等于我们跑一趟取回来,你怕啥哩!” “好。一万二就一万二,这个账,老子背了。”景丰山一拍桌子说。 “他姑夫,这可不是娃娃们耍过家家的事,你掂量妥当,耍下猴儿就是戏,你心里要有个准数儿哩,万……” 灶保姐提起茶罐往景丰山的茶碗里一边添茶,一边急急地说。 “妈唉!姑夫也不是三岁的憨娃娃!”家虎一句话挡住了他妈的话头。 灶保姐说:“这么大的事情,又不像走阿舅家当亲戚,万一出点麻达……” 家虎直戳戳地说:“你说点吉利话!” 经过连日的准备,景丰山终于实现了他做了一辈子的想当金掌柜的梦。汽车、砂娃都雇好了,家龙家虎成了他的管家拿事。景丰山把一切权力交给他们俩,自己只管当掌柜的过瘾。 起程的日子定在了老佛爷释迦牟尼出生日的第三天四月初十。本来就想在四月八那天走,但砂娃们不干,他们有的要去塔尔寺看晒大佛和喇嘛跳“邦邦’,有的要去庙沟里看跑马。初九又是个出门的忌日,“七不出,八不归,初九出门犯忌讳,”就只好初十上路。 初九的那一天,尕麻娘蒸了一天的馒头,这是景丰山交待了的。馒头要大,小了不成。 尕麻娘一个人忙不过来,景丰山说,那就叫灶保姐来。尕麻娘不愿意,景丰山说,那就你一个人蒸,蒸坏了我再问你。 尕麻娘说,我央及个旁人。景丰山说,这事儿旁人插手不吉利。尕麻娘问:灶保姐不是旁人吗?景丰山说,灶保姐的两个儿子是我的管家拿事,她咋成旁人了?尕麻娘一拍面升子说,那就把那个骚皮皮叫来吧!反正不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你心里不舒坦。景丰山说,都由你的尕嘴儿说了。 这一天,尕麻娘和灶保姐一个人揉面,一个人烧火,整整忙了一天。这一天她俩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最后,灶保姐从花园里折了个打泡儿花的骨朵儿,蘸了红醋水水,在每一个馒头的尖儿上点了个红丢丢儿的花。尕麻娘忍不住说:“我啊么就没想到。”灶保姐对尕麻娘友善地笑了一下,说,“他娘娘,我家里去哩,那两个娃娃的被儿拆洗了,还没装。” 尕麻娘拾了两个馒头放进一个条子笼笼里,塞到灶保姐手里说:“你拿上去,叫娃娃们尝个。” 灶保姐说:“吃也吃了,拿啥哩。” 尕麻娘说:“也不是啥金贵东西。” 灶保姐说:“丑么不。” 尕麻娘说:“丑啥哩。” 尕麻娘又说:“明早儿你再来一趟。” 灶保姐“嗯”了一声,提了笼子出门了。 尕麻娘送灶保姐到门口,看她走出了巷道,就骂了一声:“骚皮皮!” 这一天,景丰山一天没进家门。 头天晚上就装好了车。初十早上,家龙家虎带着20个砂娃来了,就要上车,景丰山说,先都进院去吧,砂娃们就进院了。 景丰山叫家龙家虎从隔壁人家借了两张大方桌,摆在大门口。又叫尕麻娘和灶保姐把馒头端出去,像垒石头似的垒成了一座小山。 “上车吧。” 景丰山激动得声音颤颤地抖。家龙家虎就招呼大家上车。 砂娃们挨个儿一个一个地出了大门,每出来一个,景丰山就让尕麻娘和灶保姐往砂娃怀里塞一个馒头。他自己则学着孟牛头的样子说:“囫囫囵囵出去,团圆囵囵进来,抱出去个大馒头,滚进来个金元宝……” 之后,景丰山也要钻大卡车车箱,家虎说:“掌柜的,你坐汽车头吧。” 景丰山灿烂地一笑,就进了驾驶室。 关车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尕麻娘和灶保姐。 “你们等着,最多两个月,我们赶回来过六月六!” 汽车哼了两声,启动了。 “哎哟,忙昏了头,那个老东西的一个主袄纽子断掉了,缝哩缝哩地忘缝了。” 尕麻娘一跺脚说。 “我缝给了。”灶保姐说。 尕麻娘就如挨了一闷棍,她看着灶保姐收拾好东西,又朝她友善地一笑,走出巷道口,拐弯儿不见了,才回过神来。 “呸!骚皮皮……” 尕麻娘又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未完待续) 编辑:原野 井石原名孙胜年,号煮字坊主。青海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员。省非物质文化保护委员会专家,青海民间文化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当代作家。 《昆仑文学》编委会成员 顾问:李成虎 主编:原野 副主编:向墨毛宗胜 众说纷纭栏目编辑:毛宗胜丹枫 人生百象栏目编辑:李牧李俊红 云卷云舒栏目编辑:韩有录郭荣瑜马光明 诗海浪花栏目编辑:昆仑马可林成君 校园文学栏目编辑:海芝蘭 实习编辑:王雯 法律顾问:马龙 主管:中国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主办:昆仑文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yfyl/5780.html
- 上一篇文章: 涨姿势别小看汽车轮胎上的平衡块,作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