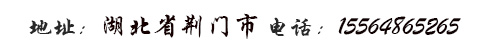大河沿
|
54年噶互助组,55年秋天进入小社,57年并社,58年“大跃进”入人民公社------辽远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一年的地瓜大丰收,地瓜井子装的满满的,村有根大沟,把底下清吧清吧接着把地瓜倒里面,大地瓜蛋一个一个的吃不迭。那时候大队部有了摇拉电话,些小孩瞅空跑进去摇拉摇拉两下赶紧跑。种粮上南蓝村去买牛,买来家一头瞎汉牛。队里的小马是翟文的爹去买的,回来来跑了。59年60年61年62年是天灾,成天下雨满坡是水,春天刮大风秋天下大雨,春天旱秋天涝。地瓜都冻了烂了,地瓜井子使棍子戳戳一戳到底。再拾来家扒扒皮晒晒,上碾拤拤团弄丸子吃。60年挨饿,翟文上初中,在学校自己种菜吃。61年春天刘邓路线分田单干没分完,集体干活,瞅空干自己的。后来又收回去了,他想着路西有他二爷爷的块地,他捞不着上学了,在那翻地瓜蔓子。种粮的爹上坡送粪,下半过晌还有趟粪,推小车装上了觉得肚子害饿了,家去看看饭笊子管什么也没有,就喝了一碗水把趟粪送去了。 62年开始生活好了,地瓜地瓜叶有的吃了。芽瓜亩产七八千斤。苞米一亩地最多达到三百斤,没有化肥,种的又疏,一步一墩,一步一墩,产量拿不上去。一个人一亩多地,苞米三百斤,麦子三百斤,交上公粮就不够吃的了。这都是死数。栽芽瓜八月初一开沟,好挖就去挖着吃了,地瓜蔓子也不舍得撂,锅底下馇着地瓜,顶上蒸着地瓜叶蛋子,很少有饼子,就地瓜面多。都吃够地瓜了,地瓜胃酸分泌过多,很多人有胃病。种粮的爹上坡使牲口,间歇的时候蹲在地头上用拳头顶着心口窝。他六叔说:种地瓜种到几时穷到几时。割倒麦子栽地瓜,虽然有吃的但是没有烧的。做饭没有草烧,上青岛市里去买煤来家烧,推着小车上那走,那是什么滋味?!那时候的煤光荧荧着发白,无论风县怎么拉都灼不上个火苗来,热水是盛在盆里搁在过梁子上蒸的,光热不开。喝半生不熟的水小孩肚子里长虫子。种苞米吃了苞米还有草烧。苞米打下来来年接着再种,就像它孙子穿着它爷爷的鞋,大粗棒粒儿净短短,没有产量。 割肉要肉票,做衣裳要布票,棉花要棉花票,买根线还要布票。一年到头皮扒皮,肉扒肉一条裤子一个小褂,伏天还有条裤子头,上河洗澡晒在沙窝上,半干不湿也就那么穿。最少的时候一年一个人三尺三的布票,种粮领布票的时候说:他一米九的大个子,做条裤子头还不够!队长说:他也没有办法,就这么些。到了年底老的(父母)真是发愁,小孩连身衣裳都做不上。大龙的娘和她婆婆打仗,大队分布票叫她婆婆领家去了,大龙的娘去要,她婆婆不给她,她非在要,在门口吆喝起来了。过年分油条,公社经理来分,一个人能分两股油条,过年好供养碗。 64年十月四号工作队下乡进农村了,搞“四清”斗他爹他看见他五叔在家哭。六月十五号以前为“四清”,六月十六号开始属于“文化大革命”。“四清”的成果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谁也推翻不了。65年“我的一张大字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艺界全部打倒了。大眼是67年遣返来家的,头一年腊月二十四,还有两天就是围子里集,在文化室开会,叫大眼做记录,他们在东边台上站着说:“四清”工作中政治不如走马观花,要以经济为主……十月四号工作队进村来了个技术员,烟台农业大学毕业的,叫春雨贤仁,来培植苞米种。他看着翟文干活仔细就叫他跟着他。春天种苞米两里公两里母,公长得快母长得慢,两种相差六七天。到了岫穗的时候,先把母子的穗绞去。公子穗上岫得花粉就像飘些粉子一样。头晌八点到十点的空,他拿着个细箩,底下垫张报纸,把花粉打吧在里面,最后把花粉落出来,找个家什放上。稳在小竹筒里,使个网垫着,他就腆着脸挨棵往母株的瓣上的缨上拍打,金色的光芒渡在他的身上,暖洋洋的,每当那时候他都有梦幻的感觉。种的时候把母本掰下来做种子,公本结不了几个粒,就不要了。第二年就可以种了。第二年就亩产七八百斤,那时候也有化肥了,换了新麦种,麦子的产量也高了。但是苞米种必须每年换。从那个时候就一步步日子好过起来。不是74年就是75年在叫翟文上海南岛去培植苞米种,和南王珠一个人一块,是院的连襟的兄弟。到最后没去,后来听说从平度找人去学习的。 65年开始挖沟,西坡搞规划,砸撅撒灰线把地割成一方一方的,中间挖沟好上外排水。成冬天在外边干活,第二年正月初三就开始了。在饲养室有个坟是他老爷的,67年秋天他和他爹把它起了。68年,69年在文革上,他为什么想的这么清楚,他二哥当兵,春天来的信函,准备入党要进行家庭情况调查,信函不上围子里送,而他在青年团开会。后来公社派人陪着南京军区来人来调查,先调查他五叔,他五叔在那喂牲口。69年清理阶级队伍,70年整党建党,建支部,那时候住户吃饼子,到秋天去刨豆苲。70年他结婚。在那三间老屋里,他叔的俩媳妇都在那结婚,他大哥在那结婚,他结婚准备在西间。他娘的大衣橱,他大哥结婚的时候使得,他结婚还使这个大衣橱。翟文去买了两张布票,一块钱一张,一张一尺。叫派出所所长抓到派出所去了,说他贩布票,他说叫他从他身上翻中了,能翻出第三张就算他投机倒把。确实没有第三张,到晌午头就把他放了。买个吊镜买不着。上沙梁听亲戚说上毛子埠花五块钱买个吊镜,踩着冻凌去了,挨号没买着。腊月初四结婚,听说即墨商店有两块钱一个的,就是小。他就骑着车子上即墨了。买回来在脊梁上背着在河沿上,像背着媳妇一样要紧。一辆赶马车的牲口躲车把马惊的从他身根过去,把他吓得像那匹马一样,边上有棵杨树他俏皮的上去两手把它箍住了,两腿夹着车子,就怕碰着他的吊镜。赶马车的赶紧把马勒住,把他扶下来。转过年来有了第一个孩子。 河东被龙湾头(村名)外边扎了一层柳子圈了起来,接着压上了树,没有几年长成了树林。55年翟文十岁,上二年级,能撅着筐子拾粪了。那年夏天大沽河发水,水流湍急。水从东边来,在磨坊下边一旋上东去了,而叫东边树林一顶,顶到这边河沿上,而从这往南一旋又顶到了张院(村名)祠后。有个人穿着裤子头要扎个猛下去看看,人们要使根绳拴着他,他不用。他一个猛扎下去接着拱上来了,说:“坏了,拱进河沿木是(很,特别)深了!”在现场有个区级干部背着匣子枪,接着拿出枪来朝着天上“啪啪”两枪,人们都惊了!吓得都寻思出了什么事了?!干部接着拿出小话筒吆喝布置任务,各生产队拉麻袋,拉草包子,没有人敢不听,都马不停蹄,急三两火的。各地都推着大木车子一齐往这送,麻袋和草包里的地瓜还没有一揸长。河沿顶上净蒺藜,都赤着脚穿着裤子头,下着小雨连土加泥。俩个人一督劲就把麻袋发在肩膀上,扛达扛达到那里稳下了。水太大了,撂下去的麻袋眼瞅着就旋走了。马上打电话叫小高(村名)送铁丝,这边砸橛子,上东沿砸橛子拉上铁丝把麻袋拴上使钳子扭着。还挡不住就割树,怎么得劲怎么割。割了就拖河沿顶上挡着水,水浮流浮流的,不挡着就要逛荡过来。水到了河沿顶了,真吓人!最早的房子是土坯的,也使青砖,窗口下面有理五层的,七层的,九层算多的。都说一个笑话,一个垞盖了四间屋一共用了八个砖,但这是真事。六几年买不着瓦还使草披,翟文学着披屋,上边三趟瓦下边使草披。后来从桃源(地名)开了口子,水势得到了缓解。家和村庄安然无恙,所有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大沽河一开始叫一迈河,河沿净矮矮,这边能望着那边的人,也就一人头高。后来组织民工加固起来,修了好几期。 53年搞初级社,修桃源河。他记得清楚是因为他爹修桃源河才回来,在家吃饭,厢屋起火烧煞了他家一头小驴。55年8月修大沽河河沿,乡公所在小高(村名)按着。河沿一截一截的分开,按区划分。围子里对着的一截分给了城阳古庙头,围子里属于胶莱八区,分着了前韩(村名)一截。 修河沿都是出去河沿五十米挖土,都是大筐抬得。四四方方的大石头,标着四根杠,四个人四根绳提溜着打夯,热火朝天。半根草根都得拾出来,长长的大河沿都是大筐抬出来的,就像小燕子垒窝一样。秋天时候搭屋子住在场院里,吃的是饼子地瓜大咸菜,自己捎着饭来的,在那干活在那吃饭,有专门的上这送饭的,使小拥车推着。北边养鸡场有个湾就是修河沿时挖的,他姑姥娘的坟就在人家的天井里,他二爷爷的媳子是他娘的亲姑,小时候他爹都领着他去上坟。河沿修了大约两月,天冷的时候恰好修完了。 小队长没有干的,公社来人动员动员这个,动员动员那个。谁上去糊弄着干一年在就不管了!没有人打谱留出一部分来做下一年的生产费用。集体时候责任都在队长身上,社员干活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去一天记一天的工分。他在生产队管场院七八年,在下雨了晌午头他溜胡同转着去叫人,社办的不管,人家在家睏大觉,分粮的时候如数分粮,都在场院里攀伴。家里一套场院老婆都他照望着。晒豆子得看天,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看着阴天得提前拾捯好了,该垛的跺,该盖的盖。拾捯不好下雨就得抢场。那时候你家有儿能推小车了,你就是老头儿了。有儿能推小车送粪了你就上场院中了,人到了四十五六岁身体就拉到了,五十来岁就弓弓腰了。那时候老人记工分打发小孩拿着本子去记,这会寻思起来那些人干了半天活回到家是真的不愿意动弹。 牲口有个瞎汉爹,有个小脚的的娘,和骡子弟兄俩个,他大嫂子当家,一有有了四个孩子。一共有四间屋,说不上个媳妇。他找好人说好去学风县,他大嫂子不叫去。在副业上杀树。四周都去杀。三个人上村里去买树,使地板车拉来家。出去杀树五毛钱的伙食费,远的八毛,近便的没有。七十的媳妇原来媒人要说给他来,谁知道七十去卖细粉(粉条),她就看上七十了。对于媳妇他没有条件,只要人家能看上他就中。他第一回上他丈人家去的时候,她穿着自己织的布自己做的衣裳,编着两根辫子。她叫杏嫚儿,但是没有人叫她杏嫚儿,都叫她牲口媳妇。杏嫚儿就像是她娘家的好时光一样使小手绢包了起来,搁在了炕头或者箱的一角。 从她娘家来了一个要饭的,说他村有个嫚儿说在围子里,家去就跟人家说,杏嫚儿说个垞穷得!三日上就吃地瓜干。其实他们不知道,他家六日就赶集买地瓜干来家好吃了。分家分了两间屋,天井还盖了一间厢屋,厢屋外边依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烧草。她在胡同里缝被,人家笑话她,怎么上街上来缝被?!他们不知道,他家的炕上和天井里就铺不开一床被单。家里有块场院,牲口能一年种三季。春天先栽萝卜秧子,打萝卜种,拨了萝卜种土豆,出了土豆种白菜。打了萝卜种子上东海沿去卖,还得先佘着。但那时候最后钱都能收上来。 围子里的风县出名,最早的牌子叫“義新昇”,风县上都卡着戳。牲口一开始都说好要去学着做风县,他嫂子不叫他去,他就上了副业。上四周的村里买树,杀树,使地板车拉来家。送风县上沙子口,上海阳,上旧店,上大泽山,送趟风县记三天的公分,是个甜差都抢着干。大队出去外交定下,他们就推着出去送。从青岛回来接着上沙子口,上沙子口就得八点多钟了,上了河沿就发愁,光跟你说说大体方向,要自己去找路。上沙子口送风县回来接着打返回,返回到沧口汽车站。早年使马龙车,铁盒子像个小集装箱一样。扒火车不用花钱,到了蓝村从西边转出来。上青岛去偷上两页板子,把风县送去,有些碎的风县给人家扎固扎固,人家给点钱,余外弄点钱自己出去吃碗馄饨。那时候吃碗馄饨非常不容易。修风县是个门奇,舌头掉下来按上,嘴子掉下来订上,把风县卡了就嚼嚼扬子饼泥上。有一回上旧店送风县,趟着风歹势,一刮能把车子掀翻了,走不动了,到了梁谋就住下,碰着演电影出来看电影。 79年牲口有了他大闺女,那年他正选上大队长。他在队里不听呜呜,没有办法叫他当小队长。 81年二月二十有了二嫚儿,自己盖屋出来住了。三十八公分的墙,没有水泥只有白灰把屋梢嵌嵌缝。河沿里的树林长起来了,从树林买的树,十拉块钱一棵。他娘偏瘫了,秋天把她背在新屋里,次年二月十一去世。那年分麦子最多,有白面了,但是娘再不吃了。 七三有先天性心脏病,初中毕业了,他娘来找翟文,说:看看这块东西能干什么?翟文寻思一顿,快叫他看水去吧!谁知道他聪明,圈着弯着都修上水溜子,想浇哪就哪开口子,他自己在坡里成宿睏觉。本来是照顾他,给他记个妇女的公分。没想到他活干成这样,他爹又不中了,来找牲口要工分,在场院小屋吵吵起来。。 娘结婚后上骡子家去,看见她躺在个凉席上,一床褥子盖到半截,筷子和双在炕前站着,鼻涕啷当的。她有气无力的说:敢自我还能看着他们成人?!分家分了两间屋,姥爷住半月就来一趟,家去就叹气:看看恁姐姐什么时候能盖起栋新屋?!叮当和叮铃是一年的,叮当的生日大,庆比叮当大一年。庆的大爷的闺女叫小蔷,她亲煞了叮当,成天抱着她。冬天叮当的小脚冻的针凉,她就掀开衣裳把小脚搁在肉肉里擘擘,她成天稀罕的叫她小名。她爸爸还当小队长来,后来得个毛病来死了,她娘领着她改嫁了!叮当那时连一点记忆都没有,但是所有的大人都记得。娘的表妹送日子,人们都去看嫁妆,把叮当搁在炕上。炕上搁着一个大蒲箩,大蒲箩里晾着蒸出来大馍馍。等它们凉透了再在上面点上红点,红点象征喜庆和吉祥。叮当一个人在炕上围着蒲箩把大馍馍上的红点挨个抠了…… 林光叫翟文管账,他一看坏了,早乱了!庆的爹净弄邪的。叫他去送公粮回来就缺一麻袋麦子。他不承认,他说麦子是他自己倒的麻袋。翟文说,反正他记着,一点也错不了。那袋子麦子肯定上河闸了,他才在那认了个干爹还是干娘的!正月初三整地,上西围子里没有机井屋,翟文觉得氢胺还能剩,就问:恁还剩多少?他说:还剩两袋子。那恁怎么不推来家?翟文问道。他说:搁在二小队屋里。第二天他去了。七三说:末有了,叫人家推去了。他去找二队小队长,人家说:我拿着钥匙我末去。四爷爷在屋山头有棵枣树,一桶火油,两块布,几封火柴,就换这么些东西。村里一共两辆脚蹬车子,种粮有一辆,他不说他不借,他拐弯抹角地说,车子拐弯光要费胎。他家还早早地有缝纫机,但是他锁着,谁在使得问他要钥匙。西胡同里一家人分家分不开了。大的说,他分家使得个大衣橱,而老二使得个两扇的,怎么找平?!林光说:恁家还是光棍少了!六个人俩光棍子。他们不做声。林光又说:你在下生那么早咋?!你当小的,他当大的不就沾光了?!丰更不消说,猕猴两眼净鬼点子,在队里不好好干活,非要上林业,上了林业,自己攒钱买条烟送给队长,点上卯就走了,管那看树买树。锄地是把锄头一下插进土里,从土里一下拖过来,拖破地皮,草就不长了。锄头被磨得闪亮,溜薄,锋利。住工了牲口就去检查检查。都说满场老实,牲口用脚趋趋,一层土下面的草在那好好的。叫他上去一顿好骂。 院的媳妇不是包办婚姻,就是头着结婚才见了三次面。结婚以后光打仗,林光总是骑着车子去给院叫媳妇,她坐在他的车座子上,从大沙梁到围子里一段河沿儿俩人越走越长。没有不透风的墙,她公公私下里偷偷的问栓,好不好离婚?!栓说,离婚不是个事,那么离了婚院还能不能再说上个才是个问题。她公公爹本来鼓鼓一肚子气,这一句话他就撒气了!只能打个牙自己咽下去,听之任之。 80年林光下来了,李辉上了。 庆的爹弄车伤腰了,把他弄成个包队的,给他戴上个高帽子,等于大队养着他。稻子插秧最晚不能过小暑,过了小暑岫穗岫不到顶。还剩二十三亩,牲口要插,庆的爹就不中。李辉在西胡同喝酒,一个小孩过百岁。李辉说:不用管,你就家去插中了!牲口认为化肥和水都能供应上,柴油也能供应上,没有问题。稻子能打千数斤,麦子能打五六百斤,去了送公粮留下的够吃的了。骑着脚踏车子上青岛大新村换黑面,早上一早去了,换上黑面过晌回来好干活。大龙娘去了三回,两回碰上下雨,一回碰上下雪。有一回下雨她躲在厦檐底下,雨水滴答下来。那里正好有个小饭店,剩下的饭盛在两个小塑料桶里,她拿个小桶顶在头上,服务员说:你在吃了它?!她说:昂,恁给我我就吃了它。人家问:真的?!她说:昂,真的。 林光原来是文革主任,70年正式在围子里干书记,为了挡住那块沙,开始压槐树压棉槐。春天忙的不顾的,秋天一落叶,冬天就栽树。有了苹果园和树林叫林业。牲口下学想着去学着做风县,他大嫂子不叫他去学,他就上了林业。割了棉槐编片篓,使片篓盛大地瓜。都说栽地瓜不用浇水,浇水光要长根子。但是那一年干旱,林光主张挑水浇地瓜,他说:“地瓜会说话早上咱门口找咱了!”他带头挑水酝地瓜,闸子路边有个沿子湾,从那挑水。晌午头下着雨,他不撂担正(扁担)谁也不敢停下。那年都栽,到了秋天只要浇水的地方都长好麦瓜。 72年4月16有了第二个孩子,73年实行火化,大队做薄棺材,有买不起棺材的,庙西(村名)死了一个人买不起个棺材,觉得使个席卷着不好看,他老婆来问:“不好使棉槐条子编个?!”她听人家说有编的。林光留人家五块钱,买两斤猪肉带肋条,拿两棒酒,翟文和院一下晚就给他编出来了,底下使棍子担着。大队有两口棺材,就照大队两口棺材的尺寸编的。一米八九,两米来长,一头宽一头窄,前边高后边矮。出殡的时候都去看来,使报纸糊着,使担正往外抬。一共编了两,那个问人家要了十块钱,都嫌要的多了。 75年他翻盖新屋,那三间老屋有八十多年了。76年8月23分家。那时候谁家有个水泥瓮都欢喜的难受,墩地,桩篓都是存粮食的。大的八岁,才上学。小的五岁,俩口子白天上坡,上坡回来又打场。生产队里分苞米推来家汪鲜,急三两火的使擦成擦擦做着吃。擦冲勾勾着,擦得一楞楞的,馇着喝。种粮的小妹妹在家看孩子,黑天孩子睏了她在那抱着。孩子上学自己背着书包去,黑天回来孩子在门口睏着了。大侄子脑膜炎,大哥哥不在家,他医院去,医生说再去的晚了就治不过来了。 大口井,春天刮风,鸡狗粪的刮在里面。筲都稳在天井里,照着日头看,里面一些小虫子就像小幼子一样。草少不割舍的烧,水搁锅里熥熥,不开。连个五六成开都没有,虫子还没死就喝到肚子里去了。 78年开始打小机井,十米就能打出水来。打井的说这边是盆地,下边是浆板,王朱那边下面净是石头,一步步上这洼过来。有人说井里打上来的水没有细菌,喝生的中了。有了打虫子的糖三角,春天打一回,秋天打一回,小孩肚子就没有虫子了。那一年他家小儿子当痧子,赤脚医生给他打路霉素,打一针不行,又打一针还不行。头一天看着好好地,一宿接着起了一身疙瘩。四麻麻(奶奶)说回去快了不行,把块火拱进肚子光拉肚子。打两支针家里就没有了,上庄干(村名),庄干没有,上沙梁,沙梁(村名)没有。除些土垫炕前了,拉的脱水了。把他难受的!赤脚医生医院。医院医生姓郝,摁着他审他,嫌他送来晚了。他说:“郝医生,你先别说,恁得把制度改改,赤脚医生不放口俺怎么来?!”上医院得要赤脚医生的单子,医院不收,赤脚医生不开单子是以为能治好而且给他省钱。小儿子瘦的皮包骨,正好他小姨子送日子,把他留在那住了一个月,才喂了起来。79年7月19他娘去世了。他娘从小没有娘,在她姥娘手里长大的,去世的时候孩子都还没成人,一点福没享着,翟文一过年五更吃饺子就想起他娘来。80年林光不干书记了,立辉上去了。 她来的时候,丰已经被分出去了,他就有三块钱,他一下子给她了。八老嫲上队里借了三十斤麦子,做了三十个大馍馍,矫格庄他妹妹拿了十个,一共四十个大馍馍去送日子。怀着孕打了二十块钱的饥荒,九月二十三有了政委,坐月子她一共有十二块钱,还送汤米。一共吃了一个母鸡,他赶集去买的,还是个注了水的。光看着胖,切开净水。(那时候卖鸡的就知道上鸡里注水)。他借了他哥哥一百二十块钱,他嫂子不知道。怕叫他嫂子知道了,要把家里的大衣橱卖了。正好人家结婚要买个大衣橱,就卖了一百块钱。他说他保证以后再给她做个。后来真的就做了一个。她成天说他是个“憋木匠”,谁也没教他他自己也能做风县。但那时候不准自己做。 槐木结实好做面板,梧桐轻快好做风县,值钱。那时候的大衣橱就叫个大衣橱就是了,光有个木头的框,垮一张张的树皮带着木头花纹,一张张粘起来当个堵头。大树割板,小树修溜根锨柄镢柄。有一年穷得没法了,杀了的一棵洋槐树他做了几个毛耳头子卖给队里过了一个年。猫耳头子是风县里面的那块板,它有自己的尺寸,留下隙缝勒上鸡毛,它站着堵在里面,一根木杆穿过它,风县把拉着猫耳头子来回摩擦。鸡毛溜溜滑带动风来风去,催生锅头里的火焰。后面的“呼搭”是这个暗黑的唯一的窗口,风县把是操纵它的唯一机关。早来的天井都栽树,栽槐树,栽杨树,栽梧桐树,每个天井都在树的阴凉里。树是活物,每天喘气。人和树的气息在空气里融合。梧桐树生长快好繁殖,根上发个芽留着三年两年能长成一棵树,树里的汁液在它周身咕咕的流淌,跌落在天井里的枝头露出树皮里的绿,清凉的汁液在断茬头上溢出。在春天整个树冠开出紫色的花朵。远远地,像垛垛紫色的幻梦,那村庄远远看来犹如仙境。都说栽上梧桐树能引来金凤凰,没人看见凤凰,人们只是砍了梧桐树做了风县卖了钱。梧桐树不结实但是它不容易变形。像粉色的衫子,任谁穿上它,都能变成仙女。它像一个梦撑开了喇叭口释放甜蜜招惹蜜蜂和蝴蝶,放任香味蛊惑和催眠春天里人们做的好梦。 八奶奶的二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家里的地队里代耕,村里热烈的号召年轻的人去“抗美援朝”,大队队长问满场:“你在去抗美援朝还是要干什么?”才说完他就急急地说:“我要去代耕。”队长上去就从腚上踢了他一脚。大爷拿着小板凳上公社去开会,他姑的对象,就是他姑父在公社当干部,知道他不去当兵,给他把马扎子直接从窗撂出去了,不用叫他坐。来家说给老爷听,老爷吹胡子说以后再和他断亲。 女孩叫嫚儿,男孩叫小儿。有了小孩门楼上挂弓箭,弓箭出头就是小小,弓箭不出头就是小嫚儿。夏天抓瞎撞,单日一抓抓一个,双日一抓抓两个。在队里挣工分的时候,牲口听人家说她骂他,牲口去找她,她矢口否认,牲口就不给她记工分。住工以后在场院小屋里记工分,她把本子推到翟文面前,翟文不动弹,推到会计面前会计不做声,她扭头就家去了。半月以后牲口跟她说:“只要你说你嚼我来,我就给你记工分!”她跟他说:“牲口,恁家吃饭,我保险也烟囱冒烟。恁过年我保险也吃饺子!工分我搁在这里你看着办吧!”她就再末上生产队干活。 她一年都末上生产队干活了,就是说她一年都末挣工分。她心里话,快单干吧!各人干各人的,谁也管不着谁。她和牲口成了彼此的一根刺,如鲠在喉。 等有了她闺女(玲玲)的时候他家的日子就开始好过了。一集能做个风县拿集上去卖。那时候一个风县二十四块钱,去了本钱得挣十二块钱。那时候钱值钱,拿着一块钱能赶个集。肉才一毛钱一斤,苹果几分钱一斤,她逢集就领着政委赶集,在集上吃顿,吃完了管几时都拾一兜家去。 她一辈子没在八奶奶家吃顿饭。不对,吃一回饭。那是他娘家爹来给八奶奶掩屋,她做好饭他说:你家去吧!她听了笑了,质问他说:那么这里就差我一个人?!他也笑了。就在那吃了一回饭。玲玲小的时候有一回三指头捏着一个奤饼角,叫她哥哥,手里舞划着炫耀。政委看样子是馋,腼腆问她:我可以去要?!她觉得她养的是个儿,是她的亲孙子,她谁也不亲也得亲孙子,谁也不给也得给政委,所以她肯定的说:你可以去要!那孩子就去找八奶奶了。结果他去了八老嫲在锅台前里吃奤饼,一看见政委来了,抬手把锅饼拽进庄篓里。回来他就问他:要着了?!他不说,低着头。她说:不要紧,今下晚我给恁擘!咱擘带肉的。她说到做到,下晚就擘奤饼,韭菜肉的。 八奶奶的四个孩子,丰,收,富,玉。老大回来的时候落户在西北角落一个村,成为了富有的人。他的闺女送日子的时候她就送她一床缎子被面。富用手托着,托得肩膀那么高,从厢屋经过天井,天井里坐满客人。他把手心一斜缎子被面就滑落在炕上,她是个机灵的人,起身就说:“走走,”她大伯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撵着要给她大馍馍,她说:“俺不要,俺不要。”丰当送客,富找他说:“那礼也轻点了?!”丰上来一句:“地瓜蔓子拴牲口——照人来的。”富再就不做声了。麦子结婚的时候她给麦子“添箱”拿四块钱。那时候就那样。 82年单干,实行责任制,各人上心了。缺棵苗知道补补,以前没有管的。使锄锄倒棵锄倒棵,不上心。心情两样了,干活有劲了。庄户人有吃的有穿的不想旁的。 单干以后小队长都会做风县,牲口不会。他在家里半月末出门,最后决定去找李辉:“二叔,给我安排个活!”那时正好大沽河上青岛送水,他就把工程包了下来。召集了能有二十个人使铁锨在沙窝里开蹚挖沟单干以后小队长都会做风县,牲口不会。他在家里半月末出门,最后决定去找李。说好了一人一天三块钱,就怕挖八十公分深沙窝里的水冒出来窖不下管子去,商量好了所有的人一齐全力以赴朝着一个地方使劲,沙子口来人专门下水泥管子,结果很简单,没等着水渗出来管子就窖下去了!从河东下管道,从这边也下管道,一直下到大高正东。工程也很快干完了!而且挣得钱他觉得太多了,又一个人一天照六块钱开的,真把些跟着他干活的人欢喜踢蹬了。他那一回就挣了一万多块钱!自己寻思寻思就像做梦一样,不敢跟人说,俩口子在家偷着数钱。 接着他又承包大沽河砌坡工程。水从东边来,正顶磨坊下面的堤坝。沙滩邈邈着斜斜到张院祠后,东沿老是淌水。河流撵着冲着沙转着上东,所以在张院祠后砌坝挡住水,不然还往那冲。水往那一顶,接着就旋上南去了。到大高那里上东一冲又上这一旋,所以又砌了几个大坝挡着。一个拐弯水就冲着旋,所以边上要加固。下边四十公分的烂茬石,上面二十公分的块石铺起来砌成坝。它们是凝固的,坚硬的,水遇它便折头,水浸泡就长湿滑的青苔,大沽河像条龙一样被人们规范和条理起来。 在屋檐下,睏觉有炕做饭有锅,人们烧火做饭取暖拉风县。每个女人都有个锅台,每个锅台都有一个风县,做饭的女人一天三回不停的拉风县,新风县都成了旧风县,风县把都握进去一个凹耷。 每一个出生在这里的孩子,终究要一个女人追随一个男人。而这里的男人一生中无论行走多遥远,最终要葬在苹果的园。每栋屋都正南正北,东为上首西为下首,正面地上正北桌子,正北墙上过年挂诸子叫请诸子。诸子上人们穿古代的衣裳,开门见喜,相见作揖,一旁的孩童在放烟火。人们上坟上烧纸却在正北桌上上香,犹如他们住在那里。一辈一辈,过年的时候就把他们请出来,让他们享受供养和瞻仰,太平与喜乐。 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人们祭拜和供养,每个人都做新衣裳,准备礼物走亲戚,早晚放爆仗。过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放滴答急和烟花,吃元宵。二月二炒其子,三月三放风筝,清明就快到了。五月端午拴五索,插艾子,六月六新女婿看过麦。七月七织女姐姐下凡看牛郎,八月十五月儿圆,月饼圆,天底下的人儿也团圆。十一月叫冬月,十二月叫腊月。进了腊月就是年。 一生中的大事:盖屋打墙娶媳妇。胡同里的人们都会来帮忙,推土打夯理墙上梁勒苫子哈瓦泥墙,借桌子借板凳借茶碗借筷子借钱买新橱新柜新席新被子和衣裳做新郎官娶新媳妇放爆仗喝酒,每个人都义不容辞。新生的孩子用一声啼哭告诉世界他的到来,而父母却把好消息挂在门楼上,小小(男孩)是弓,小嫚儿是红布穗,因此世上多了两个属于他的节日------汤米和百岁,亲戚朋友纷纷表示,送来米和蛋熬煮愿她汤水富足,奉上鲜艳的花布守候他四季周全,以此表达人们对他福寿延绵的美好祝福。对于人死称“老”,是在一个人在人世间最后的盛事,胡同里的人都不会拒绝来帮忙,会请“吹鼓手”,大声喧哗,制造世上最高的动静,号的庄严和高亢能响彻天庭,唢呐声声却跳跃和明亮,引得人们围过来,围过来看“出殡”的。人死以后埋进土里,却把名字添在诸子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oumatai.com/zmtcsjg/5889.html
- 上一篇文章: 摩旅爱好者汪轶穿越新藏线无人区纪实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